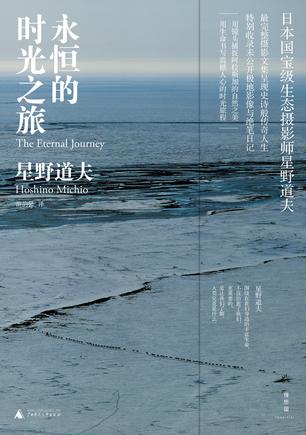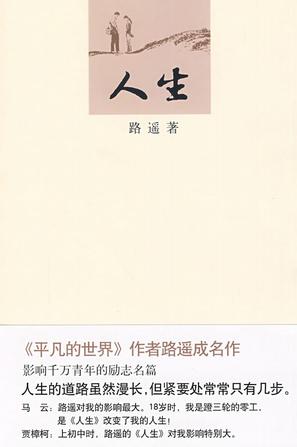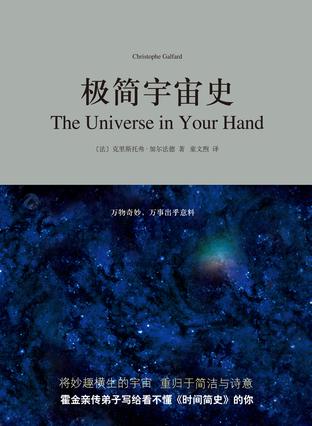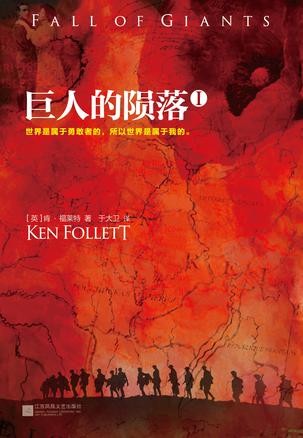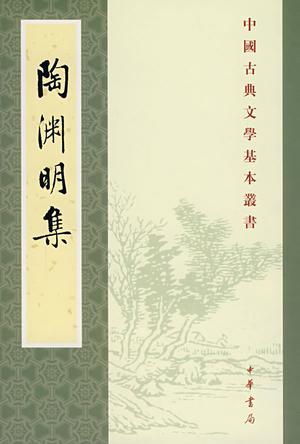-
“我们当初就是为了某些人能过上人上人的生活而打仗的吗?以前那帮人来剥削我们,现在换这一帮人来剥削我们,以后换别人来继续剥削我们。总之打仗就是在给某些人捞钱。”
-
我们开始闲聊,谈喜欢的书。她说喜欢村上春树,盼着他拿诺贝尔文学奖,但也为韩江获奖感到高兴,“这意味着我们亚洲女性终于被看到了”。我突然感到这些话击溃了我——我们的精神世界如此相似,但她却生活在一个女性连发声都是违法的世界。我无法想象一个人的身体和精神如何能承受这种分裂。
-
而在日益繁密的规则和法则的约束下,原子化的个体,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命运可言了。
-
有时候,事物的复杂性,往往并非来自它的眼花缭乱或杂乱无章,反而源于它自我复制的整齐划一。
-
鲁文·达里奥被誉为拉丁美洲的诗圣,1888年出版的诗文集《蓝》标志着现代主义诗歌新阶段的开端。概括来看,现代主义诗歌有以下特点:(1)逃避社会现实,追求纯粹艺术;(2)创造优美的形象,使用典雅的语言;(3)憧憬虚幻的境界,抒发忧伤的情感;(4)追求世界主义和异国情趣。2
-
她迷失了,惊慌失措。整个世界都将她遗忘。她睡了很长时间,醒来的时候,双目肿胀,脑袋痛得要命,尽管寒冷已经在房间里渐渐蔓延开来。她只有不得已时才出房间,就是饿得不行的时候。她走在大街上,就好像是错过了的一场电影的背景,她是一个隐形的观众,在一旁观察人们都在干些什么。似乎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
-
有时,在一旁看到露易丝和自己的孩子,会有一个不算残忍,但却令她羞愧的念头在心里一闪而过。她觉得,人们只有在不彼此需要的时候才会是幸福的。只过自己的生活,完全属于自己的 和别人无关的生活。在我们自由的时候。
-
他不怕质疑任何事情,他相信一定存在某种简单的答案——只要我们不老是折磨自己,到陌生而遥远的地方去寻找答案——而答案一直就在我们脚下。
-
相反,一个人积累的事实越多,他的努力就越徒劳,他的失败就越无望。
-
我有一次将死亡想象成一次习惯性的入眠,这是个我很喜欢的意象。关灯前我花了一两分钟,聚了聚神,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黑暗拥抱,然后将脸转向下方,手脚摊开,我的床立刻变成了一艘载我漂向黑夜之海的小舟。这种感觉非常奢华,混合着一丝难以觉察的危险气息,栩栩如生,充满诱惑。
-
所谓信仰,就是一个人决定相信他未必有理由相信的东西,并期望通过这一决定使信仰发生,继而内心得到安慰。
-
他告诉自己,活着就是要感受痛苦,而害怕痛苦就是在拒绝生活。
-
等待的时候,我做了个梦,梦里我变成了小女孩。妈妈一会儿在哭,一会儿变得不耐烦,眉头拧紧,就像以前一样。我没有撒娇,因为我不知道如何跟她开口。另外一个我飘浮在空中,期待自己能开口索取她的爱、她的注意力,我甚至期待自己能任性一把,大哭一场。但我动弹不了,只能沉默地看着自己幼小的身体。“照顾自己”像个诅咒,永远地剥夺了我的一部分本能。
-
我不确定。多少年来我都搞不明白,太多次,面对同一件事,我和丈夫却总是看到不同的东西。我们无话不谈,没有秘密,真心想要了解对方——但我们却总是看到不同的东西。 这个事实让我灰心丧气:我们到底无法通过努力来完全了解另外一个人所看到的世界,无论我们多么亲密,多么想要站在对方角度看问题,我们永远都是他人。
-
外面天色渐暗,细雨绵绵,落叶漂浮在水沟里,像一封封被撕成碎片的信,信里面,是夏天在解释它为什么逃去了另一个半球。斯鲁什金在门廊的房檐下抽烟,望着灰色水彩画般的黄昏时分镶嵌着马赛克的发光的窗户。
num196-210
共92436
相关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