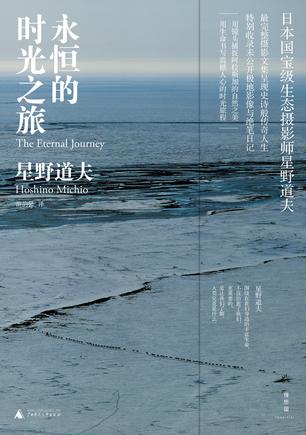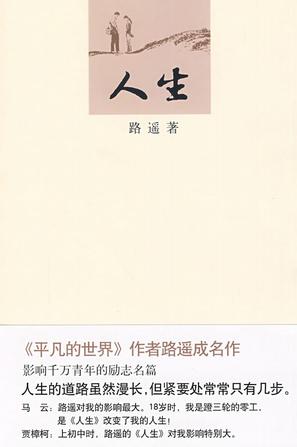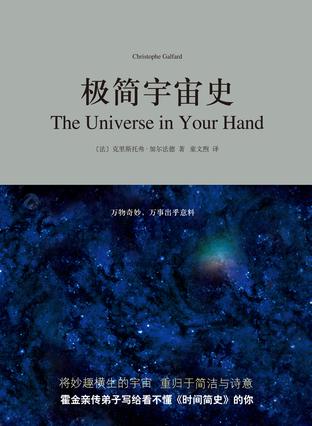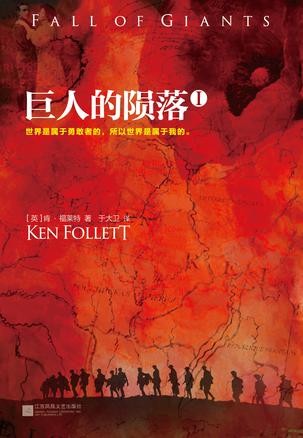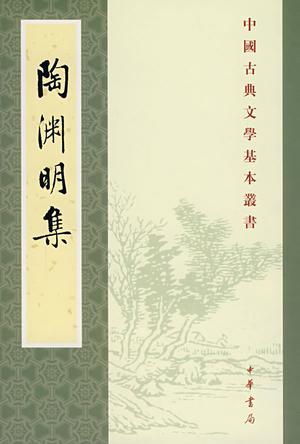-
「刚推开门,一股中药味像棉被一样迎头盖在他们脸上。厨房和客厅一角的天花板有明显熏黑的痕迹,像驻守空屋的幽灵冷眼俯视他们。」
-
“你长大了会当修女吗?”妈妈问我。她愿意让我当修女,当修女比结婚好。干什么都比结婚好,这是她的观点。
-
我们减少了各自症状发作的频率,但这并不足以让我们忍受彼此。就像我每次都能听到他打响指的声音(哪怕在几米之外也能听见),他也能在我开始拔头发之前就察觉到我的冲动。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埋伏,全神贯注地监督着对方,同时却试图逃离这种监督。然而,我们都无法忍受这种同居生活中的压抑,也无法忍受自我审查。
-
多年来,在公司餐厅里遇到同事的时候,我总会虚情假意地微笑,而从那段时间开始,我不再这么做了。并不是我不再友善,仅仅是为了顺应我的本性。与预期相反,人们并没有对此感到不适。办公室的同事还说,我最近看起来“状态不错”,甚至“更自然了”。
-
然而为什么,莉莉卡,当我们目睹整座城市毁灭的同时,其实也有一种不可告人的痛快?像是一张一张叠起来的扑克牌金字塔,或者相邻站立的一万个骨牌,花费了这么多时日堆砌起来,原来只是为了推倒它的那一刻,心底浮现的无以名状的快感?
-
一周前,他们还在超声检查中见过伊内斯,看到她伸手、握拳,脆弱得像个小蜡人。现在,医生却告诉他们她会死去。不是已经死了,而是将会死去。为此他们还得等上一个半月。等上一个半月,等孩子出生,随即又永远地失去她。
-
曾美珍收起眼泪,说:“我倒不在乎这些,嘴长在别人脸上,哪里都有嘴,又不只是榕江人才有嘴。我知道别人肯定早把我骂过千百遍了,但我没亲耳听到,就当没人说。他们说的话又不是圣旨,我恨透了别人说什么我就得去做什么,凭什么呢?”
-
她拥着薄被,坐起身,再一次感到自己如此的幼稚可笑。其实我压根不需要把自己托付给谁吧?我过得怎么样,跟去哪里,跟和谁,又有什么关系?我过得怎么样,为什么要和别的人扯上关系?
-
早纪子死了。与我相伴十七年、相濡以沫十七年的妻子不在了。这与我死又有什么区别。 早纪子的声音突然在脑海中响起。 ——还要跟你白头偕老呢。 这成了她此生唯一违背的诺言。
-
结论在死刑或无期徒刑之间摇摆。正常来说,为谋财而诱拐未成年人,最终将其杀害并抛弃尸体,乃是避免不了极刑的重罪。但是这个案子在作案过程中呈现出了许多行动的随机性,令人很难断定这是一起有计划的犯罪。虽说是情况所迫,但凶手在很早的阶段就放弃了索要赎金。而且在公审过程中,被告人也表示了忏悔和谢罪。
-
下达死刑判决对法官,尤其对审判长来说是何等严肃的问题。
-
It is better to think of thees machines as 'systems': to give you an idea of scale, it takes seven Boeing 747s to transport ASML's most advanced tool to a chip factory.
-
As of 2023, this makes ASML Europe's most valuable high-tech company.
-
在混乱不堪的大自然中,生命现象呈现出了明显高出一筹的秩序感。
-
顺便插句话,很多现代生物学家认为长颈鹿的长脖子和吃高处的树叶没什么关系,而是性选择的果雄性长颈鹿为了争夺配偶,彼此间激烈斗争,脖子长的打架更有力量。但无论如何,在上述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达尔文和拉马克其实都承生物的特性能够发生变化,并且也都承认这种变化是可以遗传的。只是他们对于这些可遗传的变异的来源有分歧。
num211-225
共92436
相关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