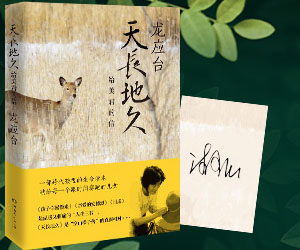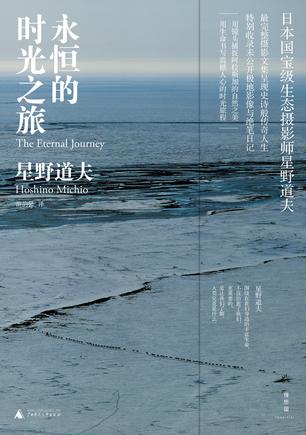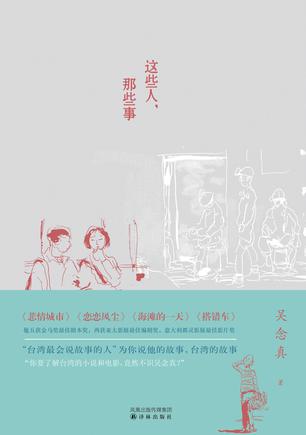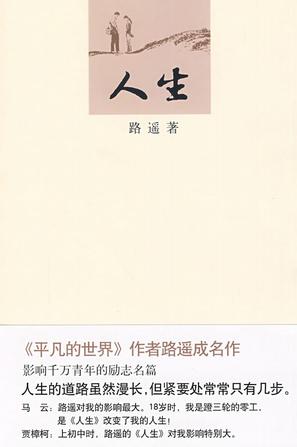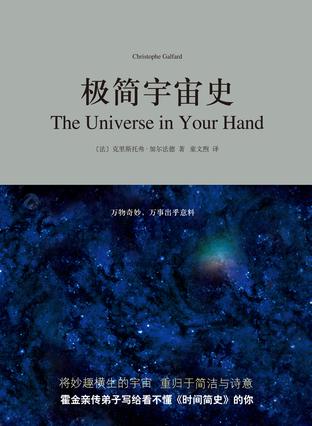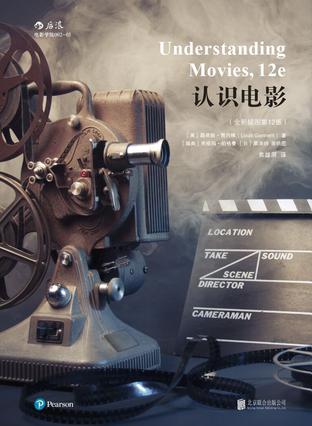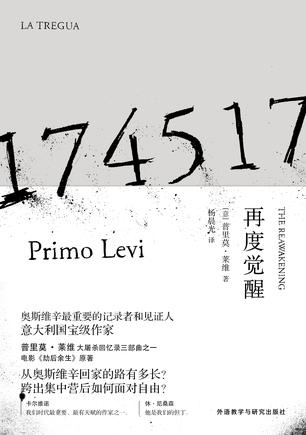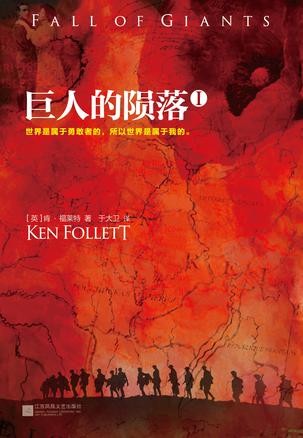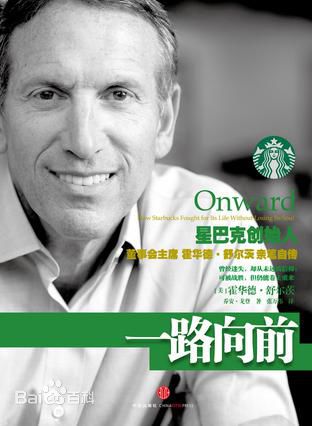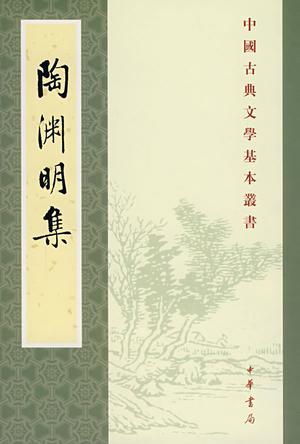-
去大公园。 哪怕只是敲出这四个字,我心里也会漾起喜悦的微波。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清楚记得初次踏访的那个早春上午,一个野趣盎然的城市公园如何俘获我的身心。
-
在我看来,A股也有这个“公元1500年”,那就是2005年。之前15年(1990一2005年),A股相对静止、规则不全、比较蛮荒,一切都较为原始;此后15年,日新月异,每几年一个变迁,十几年浓缩了发达市场几十年的经历。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计算出,1915—2015年,经通胀调整后,美国住房市场的年实际收益率“仅为0.6%”。更重要的是,这部分实际收益大部分发生在2000年之后。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经通胀调整后,美国住房价格基本持平。
-
你需要的是一种新的看待消费的角度,这样你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做出财务决定。为了做到这一点,我推荐两个小窍门,将它们结合使用,你会在花钱时完全没有内疚感。它们是: 1. 两倍法则。每当我想在某件东西上“挥霍”时,我都必须拿出等量的现金进行投资。 2. 专注于长期满足感最大化。购买体验、犒劳自己(偶尔)、购买额外时间、预付费用(例如全包假期)、为别人花钱
-
身体弱,先做力所能及之事。 等强壮了,再做艰难之事。 量力而行,正是养生的前提。
-
家长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培养出孩子照顾自己人生的能力。
-
謙卑的心,宇宙更高的力量。------通往真我的途徑。
-
也就是说,如能多食用富含酶的生鲜蔬果,就能让消化系统立即得到休息,体内的代谢酶也能更有效率地被体内其他系统运用,也才能让身体发挥自我治疗的功能,重新恢复平衡并走向康复。
-
所以,从这个因果的层面去着手,想找到一把钥匙是不可能的。
-
如果完全不接触动物性的饮食,建议每天补充维他命B12,这是只在肉或蛋奶才有的营养素。
-
低糖饮食:10%碳水、20%蛋白质、70%脂肪 ❌尝起来甜的糖、含高量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富含淀粉的蔬菜,如胡萝卜、马铃薯、玉米)、水果、米饭、面食、面包、甜点
-
但在排尿时,并不建议做凯格尔建肌法,因为这样容易导致尿路感染。 凯格尔健肌法做法必须正确,并且坚持3个月以上才能看得到效果。
-
3.纠正饮食习惯:唯一一个针对女性的营养学科学试验证明,每天喝超过1夸脱(约1升)或可乐会引起真菌感染复发。这真的喝太多了,不吃糖和乳制品是不实际的,但同时控制这两种食物的摄取量,保证饮食均衡,对身体健康很有帮助。
-
“你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围绕着试图让人们活得更长久而展开的,”她若有所思地说,“但你却没有花精力去帮助人们减少痛苦,减少情感上的痛苦,这不是很讽刺吗?” 她继续说道:“如果你这么不快乐,为什么还想活得更久呢?” 她的逻辑是无可争辩的,它改变了我对长寿的全部认知。
-
有的文人雅集,具有特色,且也并不铺张浪费,如张岱《陶庵梦忆》卷八所记“蟹会”就是一个例子:“一到十月,余与友人兄弟辈立蟹会期于午后至,煮蟹食之。人六只,恐冷腥,迭番煮之。从以肥腊鸭、朱乳酪,醉蚶如琥珀,以鸭汁煮白菜如玉版。果蓏以谢橘,以风栗,以风菱。饮以玉壶冰,蔬以兵坑笋,饭以新馀杭白,漱以兰芽茶。由今思之,真如天厨仙供,酒醉饭饱,惭愧惭愧。”
num226-240
共92436
相关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