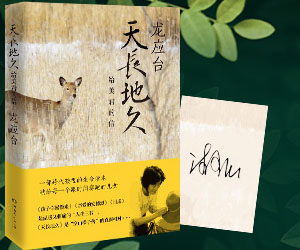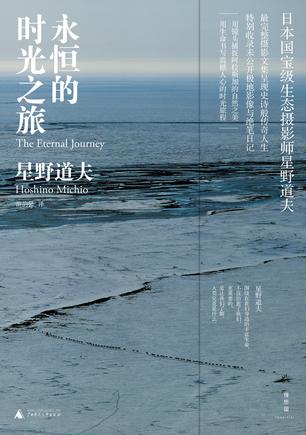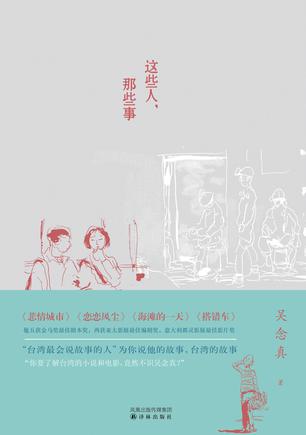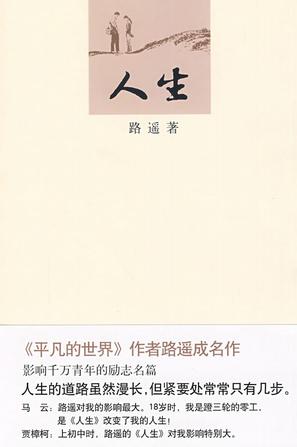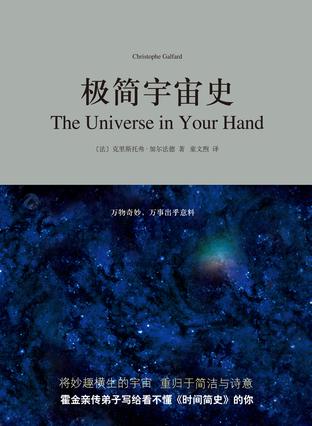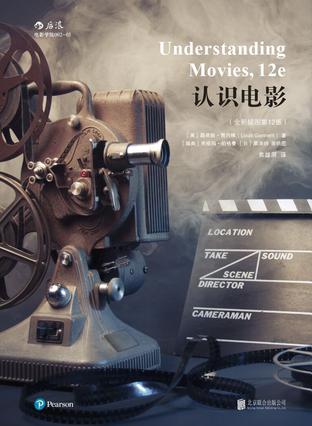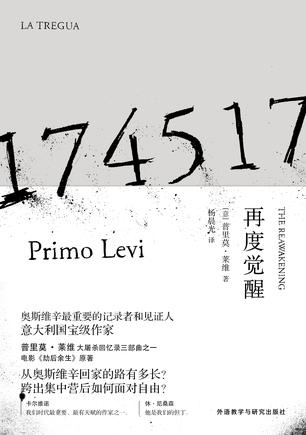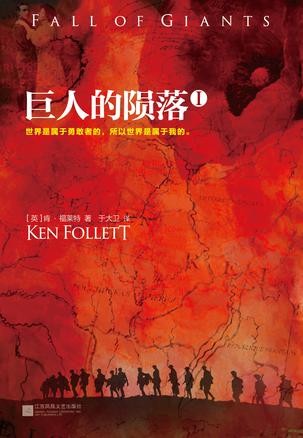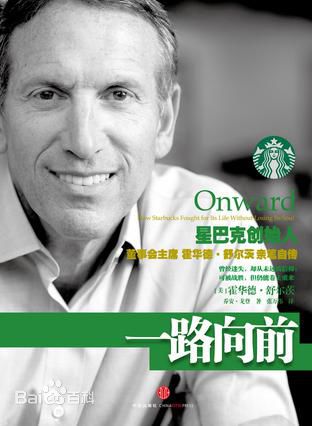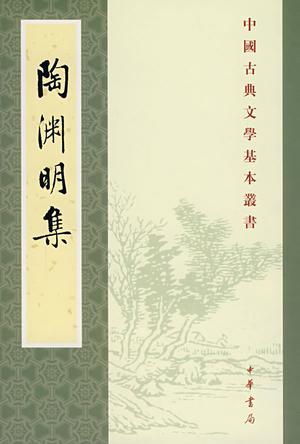-
父母中谁会先死?另一位将如何应对?我们假想父母中这位先死,那位后死,然后审视着这张假想图,它像最早的地图一样不完整且近乎幻想。更糟的是:我们说出选择。谁最好不要先死,他还是她?还有比这更糟的:我们做出选择。
-
幸福是危险的,太幸福就会招来不幸,对待幸福要谨慎小心。乡下人知道这一点。他们有自己的策略和应付的办法。他们从来不说“很好”,而是说“不太坏”。
-
爱摧毁了“我”和“非我”的划分,倾覆了旨在将存在原子化或离散的、逻辑定义的人造隔墙。如果任其发生,爱就会整合被理性原子化的生命,并提供一种神秘的整体感,融合存在的离散表征。极力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每个独立对象都在其中,你自己也是其一部分,与整体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对存在的认知态度。如此一来,爱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认知的载体。
-
但很快地,我就适应了他的步调,融入了他生活的那个具体、独特的时间之中。在这个时间中,设有时刻的概念。没过多久,时间的刻度和它运转的周期也被驱逐出了我的生活。
-
九月初的某一天,普鲁斯特先生突然对我说:“夫人,既然战争让居民们都离开了城市,我决定像往年一样,去诺曼底(Normandie)的卡堡(Cabourg)散散心。麻烦您照管好我的行李。我的手稿放在这个手提箱里。我出行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它们,这是我最宝贵的财产,绝不能和我分开。
-
就引用达戈贝尔特国王对他的狗留下的一句遗言吧:“再好的伴侣,也不会好到无法与之分离。”
-
许多年间,我被人告知应该怎么想,怎么管好自己,怎么写作,甚至由于我是个女人,男人们认为自己有权告诉我如何感受,但后来我不听他们的话,试图自己弄清楚,而他们还是不住嘴。哦,天啊。于是我开始还嘴。
-
这位女友的来函充斥着浓郁香艳的性感风情,就像是她使用的语言、使用的名字、使用的词汇,加上它们放荡直率的发音,混杂着石竹和焚香的辛辣味道,散发出慵懒而略带潮湿的气息,那是处女洁白的肉体和乌黑浓密原始隐秘的毛发的气息:
-
文学是巨大的颠覆,是对心脏的无情打击,是某种基本的勇气和鼓励,同时还是某种致命的疾病。
-
95* 有时,恶在手中好比一个工具,端看你是否看出来;如果人们想,就可以毫无异议地将它放在一旁。
-
67 他追着事实跑,像一个初学溜冰的人,反正哪里禁止溜冰,他就去那边练习。
-
欲望的表层就是:性。欲望的内核就是:权力。性是黑夜里的白昼,权力是白昼里的黑幕。
-
欲望的表层就是:性。欲望的内核就是:权利。性是黑夜里的白昼,权利是白昼里的黑幕。
-
考虑到经济情况,其实我和我丈夫都不想让女儿去美国读大学,但听说如果考上美国的大学后再去报考韩国的大学比较有优势,面试的时候有很多学生都会说自己已经拿到美国的大学入学资格了。
-
subjectivity is constructed
num1-15
共92460
相关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