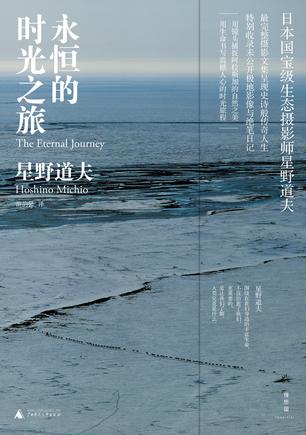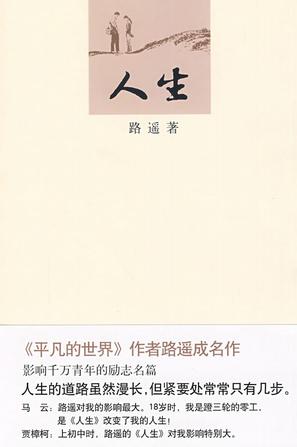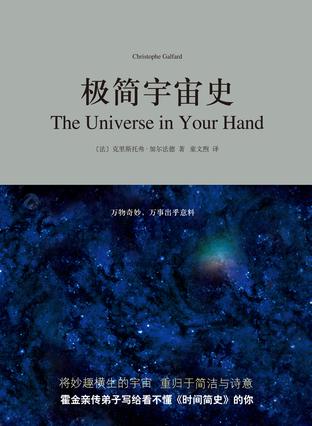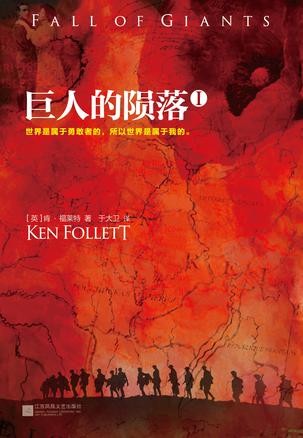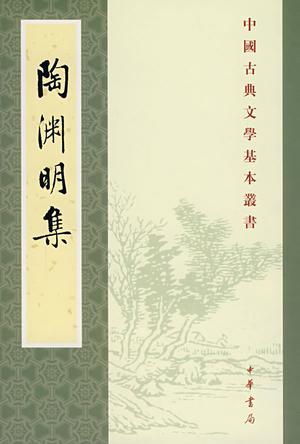-
…民国大叙事,都需要女性不仅独立自主,且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
男性本位观的女权思想鼓励女人做男人从事的事,到男人主宰的社会场域活动,却不会相应鼓励男人做女人做的事,或发展良好的女性化气质。一言以蔽之,男性本位观抱持“男人是人,女人(至多)是类男人”的心态。这使男性本位的大叙事虽允许甚至鼓吹女权,女人却始终无法挑战男性性别优势。
-
不自然则七扭八捏,丑不堪矣。 有独造而似抄袭者,有抄袭而似独造者。 闺阁闾阎,无往而非适。
-
沈子培述李星吾驾部言,榕树根洗痔疮三五次可除根,星吾之尊人亲试验也,已托关咏琴函致。
-
作为统帅,争取财政支持与后勤保障,是第一位的工作。
-
管仲在临淄开办了七家官办妓院,每家有妓女一百人。妓院吸引了大批国外来的商人旅客,这些妓院的税收最终都进了国库。后人将管仲奉为色情业始祖,就是这个原因。
-
我们必须想到,古法语的动词 trover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寻找”。虽然语史学家在其词源上未达成一致,但可以肯定,它最初是诗歌传奇所用词汇中的个术语,意思是“作诗”(而在奥克语中,诗人们把自己
-
“这个东西像是羼入了一切其他的东西之间,把它们分开,又把它们结合。我仿效古代的人和有着相似的感觉的人,称它作魔神之力。照着我通常的做法,我躲到具体的形象的背后来逃避这个可怕的东西的威胁。”———-歌德
-
随着新感觉的出现,我们也就不再具有对早先感觉的曾在状态的回忆;我们在每个瞬间就都只有关于刚刚产生的感觉意识,如此而已,别无他哉。然而,即便是已经产生的感觉的持续也不会帮助我们形成对演替的表象。倘若在声音演替的情况下早先的声音得以如其所是地继续保留下来,与此同时又不断有新的声音响起,那么我们就在表象中具有各个声音的同时的总和,但却不具有各个声音的演替。
-
但如今,一日之间所有这些都随着你的死亡而消失了,你像一阵旋风席卷一切归去了。
-
当然,不论是徐熙还是徐崇嗣的作品,在我们今天看来,依然是工笔花鸟的面貌。但正是其与黄家技法的微小分野,开启了中国花鸟水墨技法和没骨技法的先河,乃至触发宋元以来“逸笔草草”文人画的滥觞,从而也导致了中国绘画写生和博物传统的丧失,这是后话。
-
许多人都出于错误的理由喜欢一张画,或者在不明真意的情况下喜欢一张画。他们不知道画是什么意思,这倒不重要,人们的喜好常常出于错误的理由。
-
如果经济团队跟乐队成员一样没心没肺成天吃喝玩乐,我们根本不可能成功。
-
我跟我那位分分合合无数回的女友伊芳住在一起。她后来受不了我了,跟我提出分手,导致我无家可归。
-
1913年,赵元任在美国以二百二十美元,买了一架二手货琴,原价二百五十美元,分期付款,每月三块五。当时清华奖学金每月六十美元,每月付女房东膳宿费三百零五元(见赵氏年谱长编)
num31-45
共92112
相关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