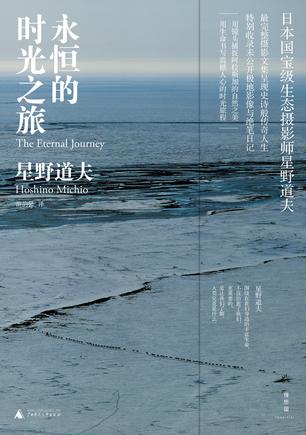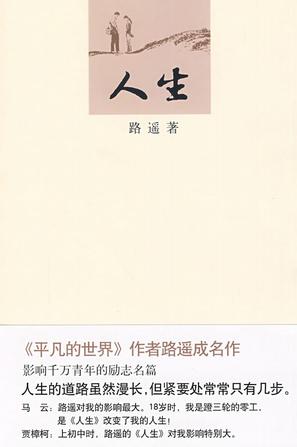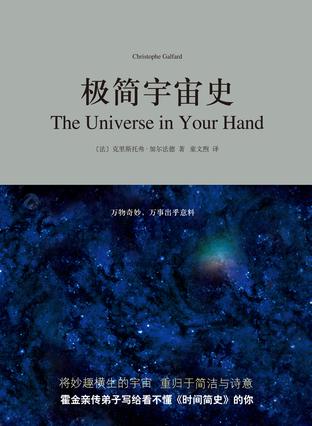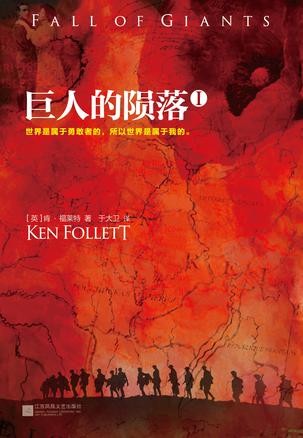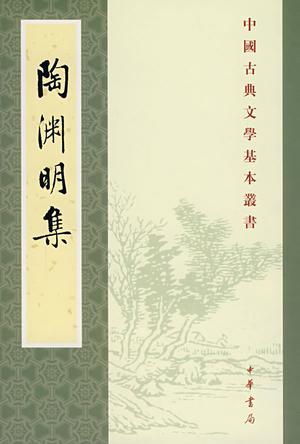-
这里,我们再一次接触到诗学的核心问题,即诗的精神性是具体行文中“变言语信息为艺术作品的特性”(雅各布森),还是美学经验与现实经验在言说中最大限度的对称?
-
诗歌作为一种生命自由的允诺,通过书写赎回了它的基本权利,或者说书写本身是对生命自由的纯粹个人的看护。
-
我逛来逛去,看人劳作,认识庄稼。黄瓜种好种扁豆,扁豆种好种豌豆,毛豆种好种蚕豆,收蚕豆时种毛豆,稻种好种麦,麦种好种稻,常识如歌谣吟诵,田间风貌变换更送。
-
一个见过那么多春天和那么多绿叶、那么多书籍和那么多飞鸟以及那么多晨昏的男人或女人或孩子怎么会死呢。
-
打开书便有风雪扑来 从一个灵魂开始的漫长冬季至今仍未结束
-
在许多的一生中 人们不过是满怀希望的司机 急匆匆跑完全程 却不知不觉 仅仅载着一车夜色回家
-
若膜拜的情愫让你想出其他比喻,你会给这对达姆达姆鼓取一对新名字:叫它们叛逆和纯爱,虚无与救赎,或者一只叫无尽的堕落,另一只是在堕落中不知疲倦的存在,那存在名字再不叫神了。你说那两面鼓,一面叫给神送葬,一面叫给神还魂的虚张声势。倘若不爱“神”,你会把其中一只叫作活着那自由的快乐,另一只叫作死亡之奴的可悲喜悦。
-
兰波就是他偏偏成不了的梦幻。他盯着闪烁发光的梦幻;仿佛见到了先兆;又看到身体复活、时间之金的征兆,故事都是有据可续的呀。他看着流星,眼里倒映着虚无和救赎,叛逆和爱,身体和文字,看它们扭在一起,彼此缠绕,舞着、偏又散了,旋即复始,划过,又灿烂地坍缩。
-
最近一次瑞土公投,是关于要不要更多的带薪休假。结果多数人认为,假期太多会妨碍经济运行,到头来对个人也没什么好处,于是投下了否决票。“我们习惯了对国家政策做出选择、做出决定,所以对权力也有责任感。给钱放假都不要,很多外国人不能理解瑞士民意。”
-
村上:就和画家在画布作画一样。画布有边缘,大家都是在边缘内侧画,无法画到边缘之外。但画家并不觉得不自由,从没想过一定要有广大无边的画布才叫自由。只要在脑中设定一个尺寸的画布,便可在其中形成一个世界。同样的道理,小说也大抵可以看见边缘在何处。否则就会发生都已经写了几十万字还没描写透彻的情况。所以,写到某种程度后自然会看见构造。
-
我们如此目睹的光景,不过是现实世界极小极小一部分。我们习惯上认为这便是世界的世界,其实并不是的。真正的世界位于更深更暗的地方,大部分由水母这样的生物占领着,我们只是把这点给忘了。你不这样想?地球表面三分之二是海,我们肉眼所看见的仅仅是海面这层表皮,而表皮下面到底有什么,我们还基本不知道。”
-
我或许败北,或许迷失自己,或许哪里也抵达不了,或许我已经失去一切,任凭怎么挣扎也只能徒呼奈何,或许我只是徒然掬一把废墟灰烬,唯我一人蒙在鼓里,或许这里没有任何人把赌注下在我身上。"无所谓。"我以轻微然而果断的声音对那里的某个人说道,"有一点是明确的:至少我有值得等待有值得寻求的东西。"
-
对梭罗来说,走了多少路就能写出多少文章,如果被关在房子里,他根本无法写作。
-
我终于弄清楚所有的事情到底是哪里出了错,答案就是它们都多了。我的意思是,除了时间、金钱、优秀的水管工,还有感谢你为他们挡住大门的人们,其他的每样东西都太多了,多到超出我们的承受范围。(说到这里,我想顺便公开声明一句:下次你挡住大门让后面的人过去,如果他们不说“谢谢你”的话,门就会砸中他们的腰。)
-
在这世上,爱情真是凤毛麟角。如果爱情出现的时候,人们真该好好把握,尽可能地善待它。
num1126-1140
共92112
相关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