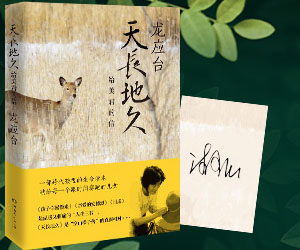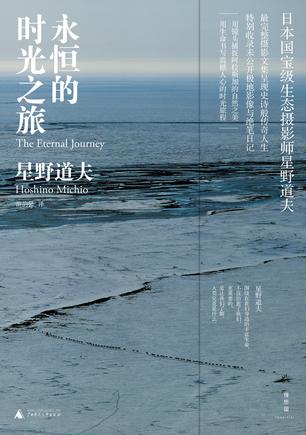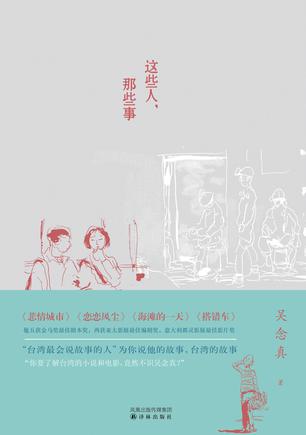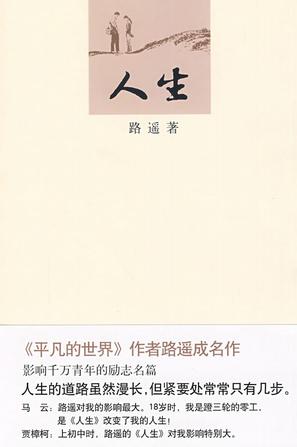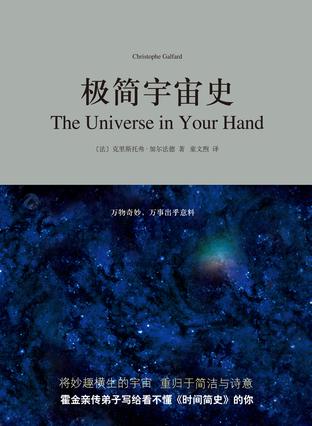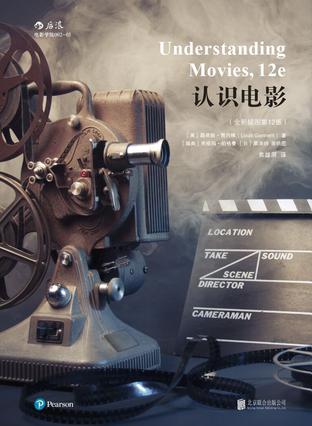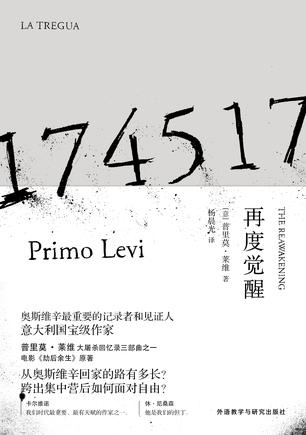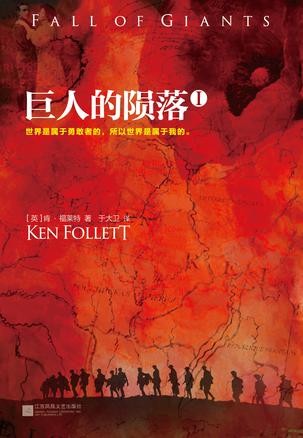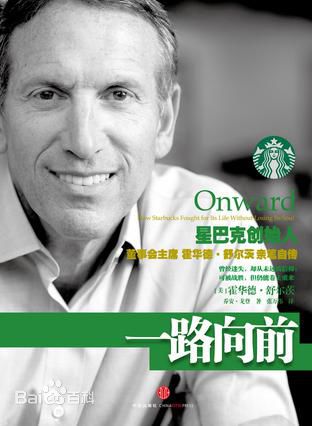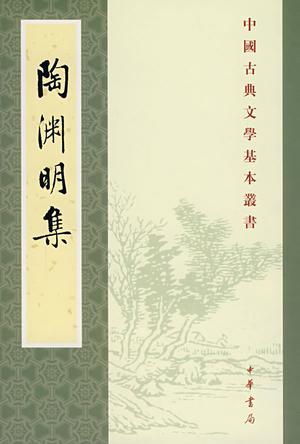-
侠客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一作上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閤下,白首太玄经。
-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
不佞曾得光绪间石印小册《北上备览》,盖当日都门导游之类书籍也。其中对吃馆子加以指导。如‘糟温’为翁文恭公潘文勤公常去之所;安儿胡同有烤肉馆,虽仅一间门面,而达官贵人、摩登伽女,多就案前长板凳,跷一腿立于凳上食之。门外排队而候之者,如长蛇阵。冬晨雪霁,此一幅‘吃肉图’,亦大可观。
-
鹪螟巢于蚊睫,大鹏弥乎天隅 注:语出《抱朴子·刺骄》
-
her uncle - a worthless old fellow enough in himself, I daresay, but he had always shown more kindness and affection to her...
-
将军第一次尊称女儿“子爵夫人”时,心里对她真是宠爱极了。埃丽诺长年陪伴父亲,替他做这做那,耐心地忍受着,还从来没有叫他如此喜爱过。
-
我果然没有看走眼,瞧你说话做事,都像是读过书的人。怕是遇上了大的难。这广州湾,离广州千里地。你一个人能过来,也是大能耐。不知是遭了多少罪。 阿云说,就是一个念头。念头有了,总有法子来。
-
发现没,杨过对郭襄也没有太多话说,他们也聊不到一起。 说得直接和残忍一点,南兰认为生活“无趣”,在某种程度上不是生活无趣,而是自己无趣,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生活只有在无趣的人眼中才是无趣的。
-
有人说‘爱情是盲目的’(Love is blind),其实盲目的人是不配谈恋爱的,因为他们不会谈恋爱。盲目的人根本不懂爱情,他们只是迷信爱情,根本不了解爱情真正的本质。爱情不是‘永恒的’,可是盲目的人却拼命叫它永恒;爱情不是‘专一的’,可是盲目的人却拼命叫它专一。结果烦恼、烦恼,乌烟瘴气的烦恼!
-
我们现在与动物保持着一定距离。变身成动物的人(被狼或狐狸附身的人等),被归类为有附身妄想症的病人。我们的文明正致力于不再将动物视为神圣或恐怖的存在。
-
“这个世界里最郁闷的事情就是,”以为真正的知识分子,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写道,“就是这个世界到处是傻瓜和庸人,而世界却围绕着这些傻瓜和平庸之辈运转。”
-
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一段话:对新奇无休止的迷恋,是二十世纪的劫难。
-
夜九时,敌暂退,婿勉力带伤行,潜入敌围,寻到遗体,无血无伤,服装整齐,眉头微锁,侧卧若熟睡,然已胸口不温矣。其时婿不知悲伤,不觉创痛,跌坐呆凝,与君珏双手相握,不知所往,但觉君珏亦正握我手,渐握渐紧,终不可脱!山后枪声再起,始被惊觉,时正午夜,皓月明天,以手掘土,暂行掩埋。吾岳有不朽之女儿,婿获贞烈之妻,慨属民族之无上光荣!
-
苏东坡说,再可怕的事,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担心和恐惧,一旦真正发生了,也就没有什么可怕了。所以,没有必要胡思乱想,不如安静下来,去经历生命的各种形态去体验眼前的现实,去用心做好当下的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一件事。在经历之中,在体验之中,在做事情的过程里,人生的奥秘就会向我们显现,不确定性带来的困扰就会消解。
-
我不是我理性的囚徒。我说过:上帝。我希望在得救中保持自由;如何求得自由?轻浮无聊的恶癖我已经放弃。再不需什么献身,也不需神圣的爱。过去那个多愁善感的时代我并不惋惜。人各有自己的理性,各有自己的鄙视,也有自己的仁慈,我在良知架起的天使之梯的顶端选定了我的位置。
num121-135
共92436
相关文摘
- 1. 李太白全集(全三册)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3. 来燕榭集外文钞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4. 汉魏六朝文选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5. 女房客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6. 诺桑觉寺 劝导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7. 入瓷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8. 越过人生的刀锋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9. 传统下的独白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10. 胡桃中的世界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11. 读库0703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12. 读库0601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13. 作个闲人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14. 灵光集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