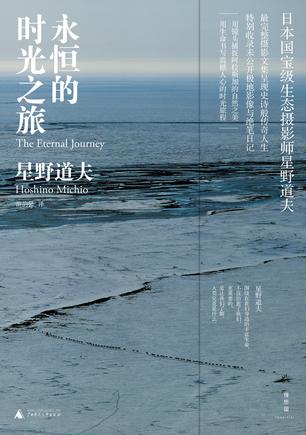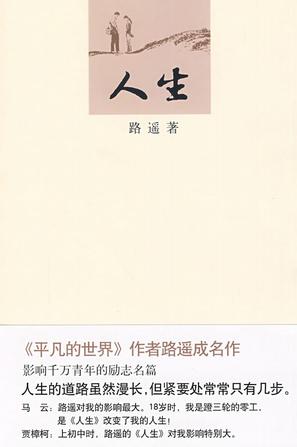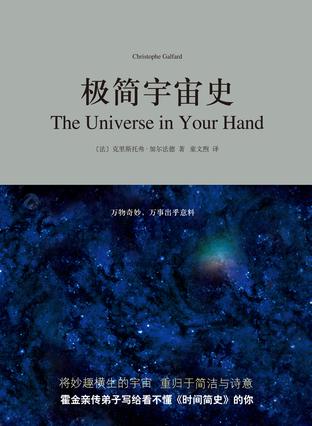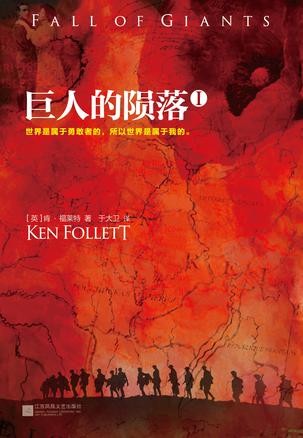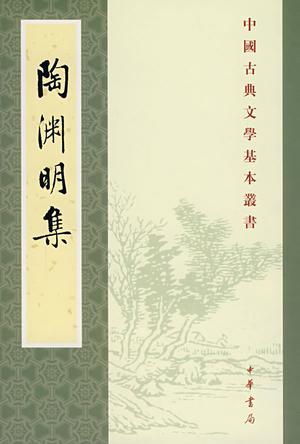-
价签?什么东西不坠个价签,朋友?你大概以为我不幸福?
-
好的拘留所是世界上最安静的地方之一。你可以夜间从一个普通的囚房区走过,透过铁栏杆的空隙瞧见团成一团的褐色毛毯,或者头发,或者一双茫然的眼睛,你可能听见鼾声。时间长些的话你也可能听到有人做噩梦。拘留所里的人生是悬而未决的,没有目的,没有意义。在另一间囚房里,你或许会看见―个人无法入睡,甚至在铺位边,什么也不干。他看着你或者不看你。你看着他。他对你默然,你对他也默然。你们彼此没什么好说的。
-
“当然。只是装装样子而已,没有其他。这里——”他用打火机敲了敲胸口,“这里什么都没有。曾经有过,马洛。很久以前有过。得了——我想,就这样结束了。”
-
总有一天,她会需要我,而我会是她身边唯一一个手里没捏着利器的人。很可能到那时我会被踢出局。
-
法律不等于正义,它是一种非常不完善的机制。
-
特里,你打动过我。一个点头,一个微笑,挥一挥手,这里那里某个清静的酒吧里一起清清静静地喝几杯酒。好时光一去不复返。回头见,阿米哥。我不跟你道别。我已经跟你道过别了,那时这么做还有意义。那时它意味着沉痛、孤寂、不可追回。
-
管别人的闲事只会惹来一身腥。
-
他应当在挪威的皑皑白雪里英年早逝,我那献给死神的恋人。他回来了,与赌徒为友,为富娼之夫,成了个受宠而堕落的男人,或许之前还干过坑蒙拐骗的勾当。时间使一切都变得低劣平庸,满目疮痍,皱纹累累。人生的悲剧,霍华德,并非英年早逝,而是日益老去且日益下贱。我不会步此后尘。别了,霍华德。
-
那东西让我想起过去,那时我还不是一只酒囊饭袋。
-
这话我听玩法律的人说过,听地痞流氓说过,也听上等人说过。措辞不一样,但意思没分别:别掺和。我来这儿喝一杯琴蕾,是因为有个人曾经嘱咐过我。瞧,我现在是在自掘坟墓啊。
-
并不是因为有奸诈的政客和他们在市政府及立法机构里的帮凶,才存在流氓恶棍、犯罪集团和打手喽哕。犯罪并非恶疾本身,而是恶疾的症状。警察就好比开阿司匹林医治脑瘤的医生,不同的是警察更喜欢施行大棒疗法。我们一夜暴富,粗鲁野蛮,犯罪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有组织犯罪是我们为我们的组织化付出的代价。犯罪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尾随我们。集团犯罪只是暴富肮脏的一面。
-
我左手边是个没灌水的游泳池,再没有什么比没水的游泳池更落寞了。
-
热烈癫狂、难以言喻、如梦似幻的爱情,一生不可能遇到第二次。
-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马洛?”
“你可以趁我刮胡子的时候喝些酒。”
“我一直在想,也许你最好打电话报警。”
“要打你自己去打。我又没什么要报警的。”
“你要我报警?”
“老天,你能不能别再惹麻烦了?”
“我道歉。”
“你当然得道歉。像你这样的人总是在道歉,而且总是道歉得太晚。”
-
我脖子发痒,所以刮了胡子,冲了澡,上床平躺着倾听,仿佛我能从黑暗深处听见一个声音,一个平和而耐心的声音,这声音使一切变得清晰。但我没听见,我知道以后也不会听见。没有人会向我解释伦诺克斯的案子。没有解释是必然的。杀人者自己承认了,而且他已经死了。连审讯都不会有。
就像《新闻报》的朗尼·摩根所说的——相当省事。如果是伦诺克斯杀了他妻子,很好。那就没必要审问他,没必要翻出所有令人不快的细节。如果他没杀她,那也很好。死人是世上最好的替罪羊。他不会反驳。
num85876-85890
共92148
相关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