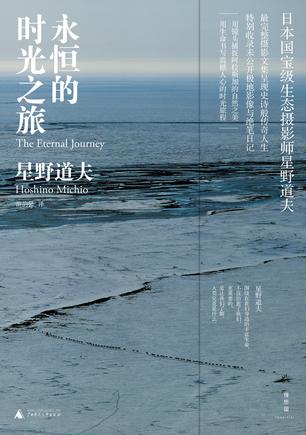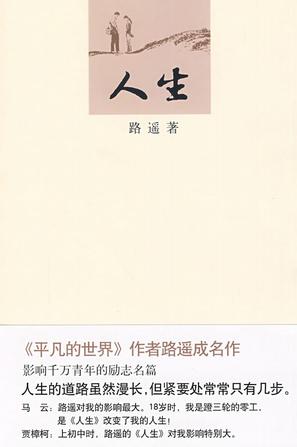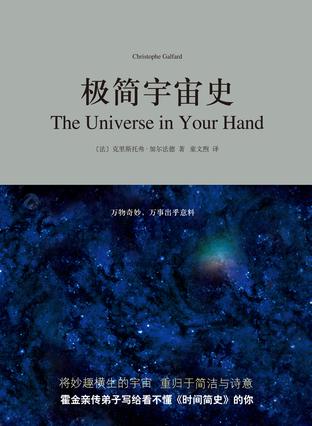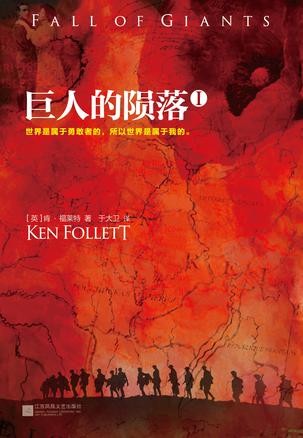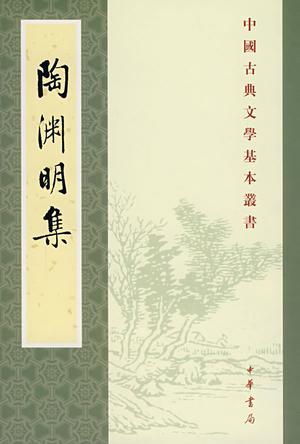-
事情简单而自然,简单而自然的事往往是对的。
-
除非你把案子了结了,否则你永远不能确定会生出什么枝节来。对吗?
-
而且大多数男人都能忍受他们所必须忍受的,事情真的来了,会毫不回避地上去。全世界的男人都一样。
-
死了,这个可怜、自私、下流、英俊但靠不住的男人。
死了,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被干掉了。
不,马洛先生,我没杀他。
-
“你会喜欢我们的新监狱。”
“你们要给我安个什么罪名?”
他想了一下,一只手轻轻扶着方向盘,一面从后视镜中看库尼有没有跟上来。 “超速、拒捕、酒后驾驶。”
“你怎么解释我腹部被打、肩膀被踢、在暴力威胁下被迫喝酒,还有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被用枪恐吓、遭警棍殴打?这几项你打算怎么说呢?”
“算了。”他咬牙切齿地说,“你以为我喜欢干这种事吗?”
“我以为他们把这小镇整顿好了,”我说,“所以善良的百姓晚上可以在街上散步,不用穿防弹衣。”
“他们是整顿了一下。但他们不愿意清理得太干净,那会把黑钱扫走的。”
“最好别这样。你会砸了自己的饭碗的。”
-
“至于你对我的态度是不是很不客气,大部分的顾客一开始不是哭哭啼啼,就是大吼大叫地表示他才是老板,但通常他们到最后都很理智——只要他们还活着。”
“嗯。”他又开口,语气同样的柔和,继续盯着我说,“你的客户很多都没能活下来吗?”
“只要他们信任我,就不会。”
-
“我还没雇用你。但如果我雇了你,这工作绝对保密。不准跟你的警察朋友谈论。明白吗?”
“你到底要做什么?金斯利先生。”
“你在乎吗?你做的反正都是侦探的活儿,不是吗?”
“不完全是,只做正经的。”
-
“他爱她。即使她六年没给他写信,即使她在他待在监狱里的整整八年时间里没去看过他,他也不在乎。即使她为了领取奖金而出卖他,他也不在乎。他一出狱就买了几件像样的衣服,然后开始找她。而她呢,朝他的肚子开了5枪,把这当作见面礼。他杀了两个人,都是为了爱她。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
-
“他还有一点点希望——如果子弹是点二五口径的话,这全看子弹射在什么部位,不过他还有希望。” “他不会要那个希望。”我说。 他的确没要,那天晚上他就死了。
-
他抬起眼睛看着我,视线落在我的头顶,然后眼皮垂下去,把眼球盖住了一半。他那样瞧着我有十秒钟左右,然后微笑了。这一天他可笑了好多次,把一个星期的配额都用光了。
-
"这一点很重要吗?"他干巴巴地问。 你也许在很多事情中能判断出哪些事情重要,哪些事情不重要,而我不能。
-
一只身上有粉红色小斑点、头部也有粉红色的黑亮的小甲壳虫,正缓缓地沿着兰德尔的办公室光滑的桌面爬着。它的触须不时地向四周探触,好像是在探测风向准备起飞。它爬行时有点蹒跚,就像一个背着太多包袱的老太太。 … 甲壳虫已经爬到兰德尔的办公桌的边缘,但它仍莽莽撞撞地爬着,结果仰面朝天跌到地上,几只细腿无力地在空中蹬着,然后它就开始装死。因为没人理会它,所以过了一会儿那些腿又蹬起来,最后它终于成功地翻过身,慢慢地、毫无目的地朝一个角落爬去。
-
他死死地盯着桌角。“在湾城。”他缓缓地说。 “那名字听起来像一首歌,在脏浴缸里唱的歌。”
-
“对呀。来点咖啡吗?” “如果我喝的话,你愿意规规矩矩,男子汉对男子汉地谈话吗?不再乱说刻薄话了?” “我可以试试,不过不能保证时时刻刻都管得住我的嘴巴。” “没关系。”他挖苦地说。 “你这身西装不错。” 他的脸又红了。“花了二十七块五。”他气冲冲地说。 “噢,天哪,来了个敏感的警察。”我说着回到炉子旁。
-
我脱下衣服上了床。我做了好几个噩梦,被吓醒时浑身冷汗淋漓。到了早上,我又是一条好汉。
num85831-85845
共92142
相关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