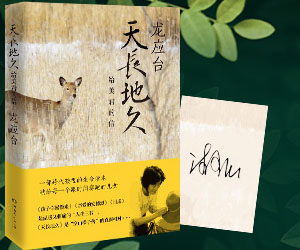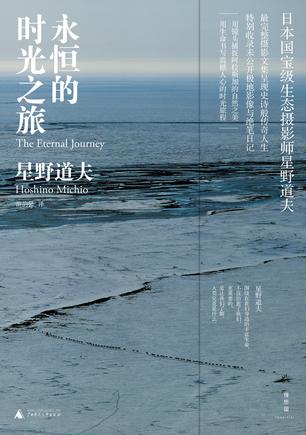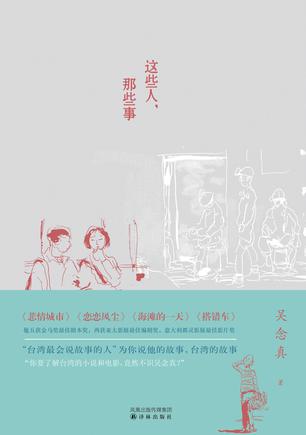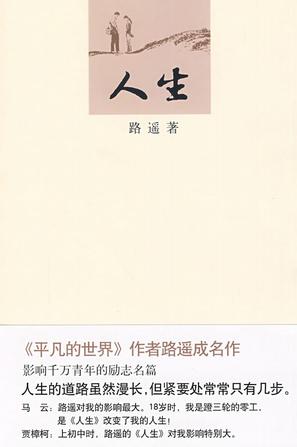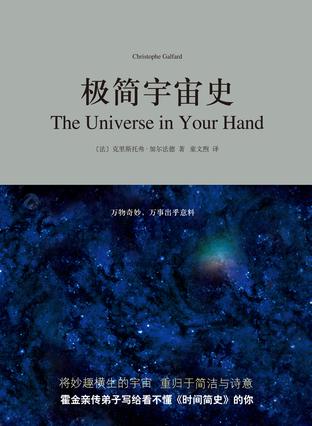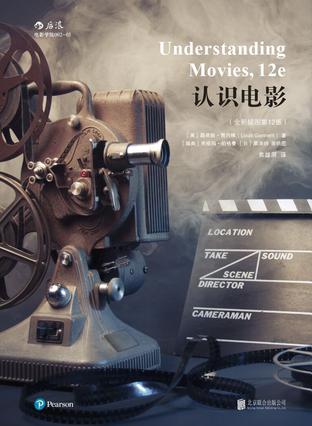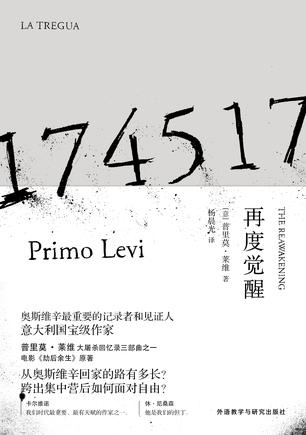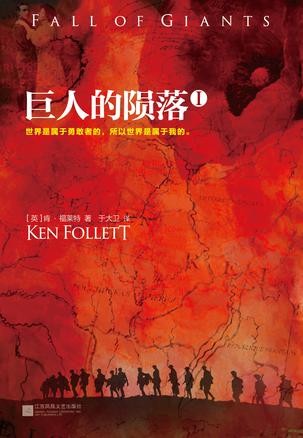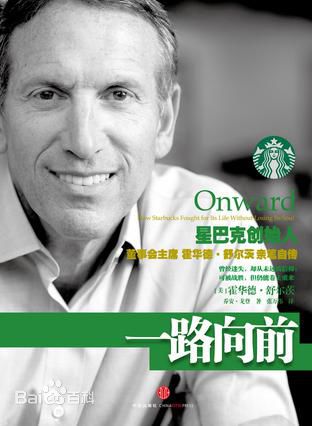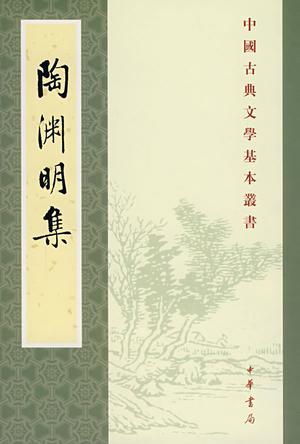-
一国一族之建筑适反鉴其物质精神、继往开来之面貌。今日之治古史者,常赖其建筑之遗迹或记载以测其文化,其故因此。
-
盖中国自始即未有如古埃及刻意求永久不灭之工程,欲以人工与自然物体竟久存之实,且既安于新陈代谢之理,以自然生灭为定律;视建筑且如被服舆马,时得而换之,未尝患原物之久暂,无使其永久不残破之野心。 修葺原物之风,远不及重建之盛;历代增修拆建,素不重原物之保存,唯珍其旧址及其创建年代而已
-
这座巨型大殿的斗栱在比例上极小——不及柱高的六分之一。当心间的补间铺作竟达八攒之多。从远处望去几乎见不到斗栱。
-
在宋代,斗栱一般是柱高的一半或三分之一,而到了明代,它们突然缩到了五分之一。
-
….第三就是提供了早期具有高台建筑特征的一种“宫观”的例证,指出了是“台”与整个建筑设计相结合的,夯土的台是作为“建筑体量”或“构造部分”而存在,并不是纯然是一个用来放置建筑的“台座”。这一来,平台配置和空间组织就转换成了另一种方式,属于“整体集中式”的建筑了。
-
祈年殿直径26米,高38米 ⋯⋯以中央四根巨大金柱象征四季,撑起圆形藻井,而二十四根内外柱分别代表十二个月与十二个时辰,其总台之数又隐喻二十四节气,正所谓“天人合一”之作。
-
所以我大概很早就有了这个创作心态,失败是常事,完美不可得。老失败就不怕失败了”——薄脸皮干事容易趴下,厚是练出来的,知道不易,知道努力,干砸了,只能说“看下一个,下一个也许好点”。
-
张艺谋说:‘那是个全民求知的时代,谈恋爱都拿本《尼采》。’遥想当年,绵绵情话从海德格尔和萨特切入,不少姻缘是从大逻辑和小逻辑、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争辩开始----即使这些争论的基础可能是生吞活剥、强作解人。只是崇拜带来的奇景,大概永不复现了吧。
-
历史,在不少女权主义者的眼中,是从男人讲述他们的故事开始的。男人把自己的故事讲成了一个连续体,而女人只在这个连续体的某些横断面上出现,由此女人的一生仿佛活在平行宇宙中,每一次自我观照都构成一种异质的经验。
-
人的观念左右了认知能力,人往往只从自我观念出发筛选可理解的事件,我们看不到我们所不愿看到的东西,女人正是这一认知模式的受害者。从十七世纪女权运动的发生开始,自我表述就被看作是女人首先要争取的权利。而与此同时,也已经有过太多表述女性现实的陷阱,在这一点上,女人自己未必做得更好。
-
事实上,构图并无一定标准,像古典主义导演巴斯特·基顿就常用均衡的观念构图;而新一代的导演则善用不对称的构图。在电影中,多种技巧均可达到相同的情绪和意念。有人善用视觉因素,有些人则喜欢对白、剪辑或表演技巧。只要有用,什么技巧都是对的。
-
因为人在快乐顺利时多半不去思考,痛苦时,才比较会反思问题出在哪里。
-
我天性竞争性不强,碰到竞争,我会退缩。跟我自己竞争没问题,要跟别人竞争,我很不自在,我没那个好胜心。
-
合理而精彩的情节叙述是硬功夫,几乎所有中国导演都在此触礁,包括陈凯歌,张艺谋等曾闯关成功的也会翻船,《十里埋伏》便是明证。
-
“您的电影震撼了我。您拥有潜入成人与孩子的感知世界的天赋,能唤醒他们对周围事物的感受,展现给他们这个世界真实的而非虚假的价值。您让电影画面中的每件事物、每个细节都富有象征意味,提炼到哲学意味,并用最简省的描写手法让每一帧画面都充满诗歌与音乐…这些都是您的,只有您的叙事手法有这种特质
num75136-75150
共90347
相关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