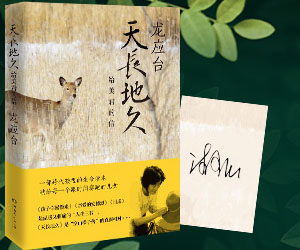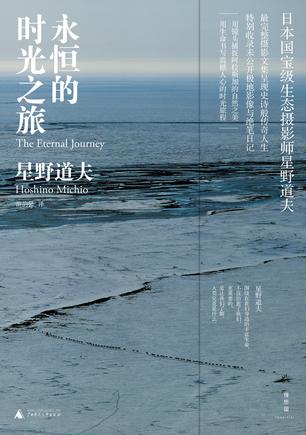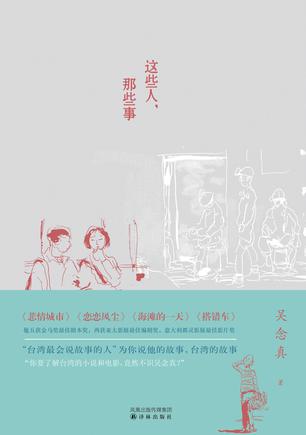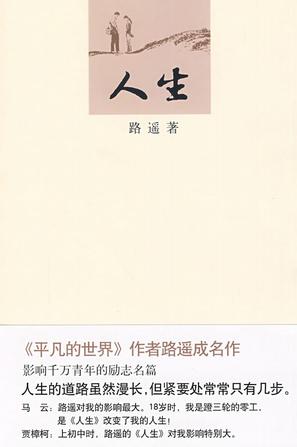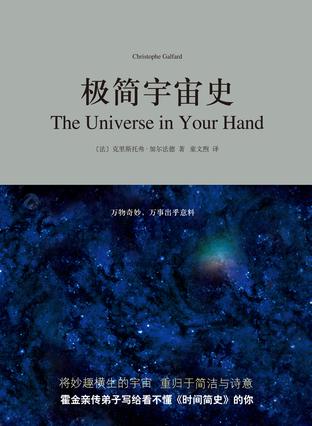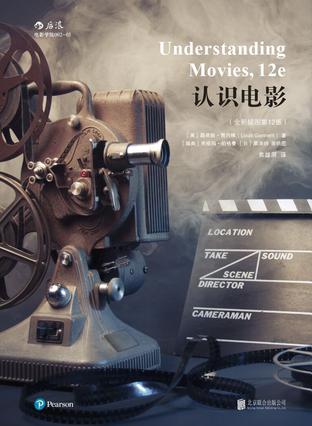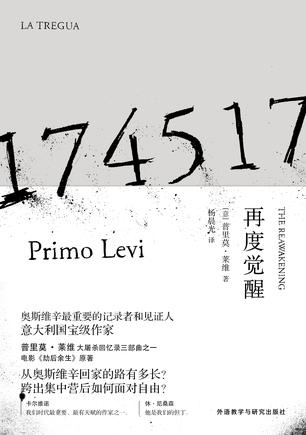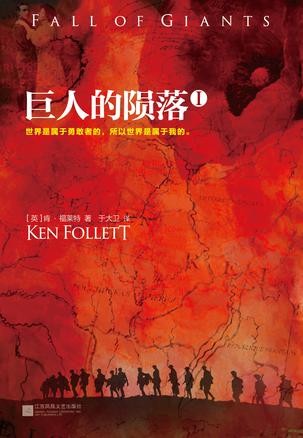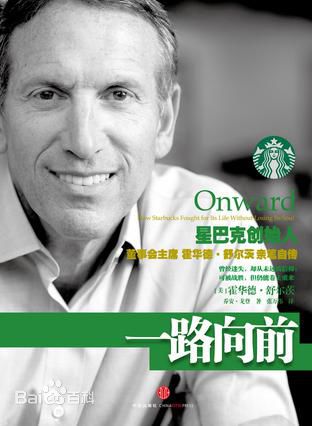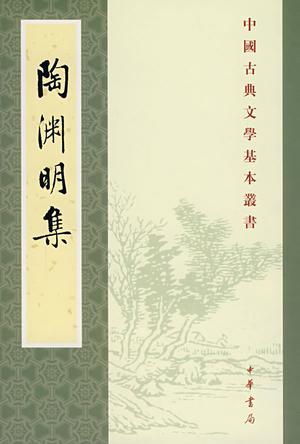-
我们必须想到,古法语的动词 trover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寻找”。虽然语史学家在其词源上未达成一致,但可以肯定,它最初是诗歌传奇所用词汇中的个术语,意思是“作诗”(而在奥克语中,诗人们把自己
-
“这个东西像是羼入了一切其他的东西之间,把它们分开,又把它们结合。我仿效古代的人和有着相似的感觉的人,称它作魔神之力。照着我通常的做法,我躲到具体的形象的背后来逃避这个可怕的东西的威胁。”———-歌德
-
随着新感觉的出现,我们也就不再具有对早先感觉的曾在状态的回忆;我们在每个瞬间就都只有关于刚刚产生的感觉意识,如此而已,别无他哉。然而,即便是已经产生的感觉的持续也不会帮助我们形成对演替的表象。倘若在声音演替的情况下早先的声音得以如其所是地继续保留下来,与此同时又不断有新的声音响起,那么我们就在表象中具有各个声音的同时的总和,但却不具有各个声音的演替。
-
但如今,一日之间所有这些都随着你的死亡而消失了,你像一阵旋风席卷一切归去了。
-
当然,不论是徐熙还是徐崇嗣的作品,在我们今天看来,依然是工笔花鸟的面貌。但正是其与黄家技法的微小分野,开启了中国花鸟水墨技法和没骨技法的先河,乃至触发宋元以来“逸笔草草”文人画的滥觞,从而也导致了中国绘画写生和博物传统的丧失,这是后话。
-
许多人都出于错误的理由喜欢一张画,或者在不明真意的情况下喜欢一张画。他们不知道画是什么意思,这倒不重要,人们的喜好常常出于错误的理由。
-
如果经济团队跟乐队成员一样没心没肺成天吃喝玩乐,我们根本不可能成功。
-
我跟我那位分分合合无数回的女友伊芳住在一起。她后来受不了我了,跟我提出分手,导致我无家可归。
-
1913年,赵元任在美国以二百二十美元,买了一架二手货琴,原价二百五十美元,分期付款,每月三块五。当时清华奖学金每月六十美元,每月付女房东膳宿费三百零五元(见赵氏年谱长编)
-
荷尔德林说:“即使我们的歌声依然脆弱,但这毕竟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
整个钢琴演奏动作实际上是连续不断的大小相扣的弧线运动,不能有绝对的直线动作。即使运用肘部和臂部垂直触键的强音中,手指的第一关节也有水平方向的运动,起着重要的缓冲作用。 总之,就是在演奏最宏亮、最有力、最强烈的音响时也要辅以水平方向的运动,使八"阳中有阴",避免直接的垂直敲击。
-
“如果我们找到宝藏,只要不是在我们自己的作品里,我们就应该把它当场拿走。”这个魔鬼这样说。毕加索掠夺了一切,但他仍是他自己。
-
康拉德认为小说家应表达“一种微妙但不可战胜的信念,相信将无数孤独的心凝聚在一起的力量,相信通过梦想、喜悦、悲伤、向往、幻想、希望和恐惧将人们连接在一起的力量,将整个人类——从逝者到生者,从生者到未出生的联系在一起”(《水仙号上的黑水手》)
-
与其寻求反馈,不如追问建议。反馈往往关注你上次做得如何,建议将注意力转移到你如何在下一次做得更好。在实验中,这种简单的转变足以引出更具体的建议和更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其纠结于你的过失,不如让建议引导你正确行事。
-
现在,全世界越来越重要的问题不是“如何让这些人吃上饭”,因为食物是充足的,有时候只是需要组织和运输。但是,要拿这些人怎么办?要如何处理地球上这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人口?如何利用他们尚未被开发的能量?他们的力量真的没有人需要吗?在人类大家庭中,这些人的地位是什么?是正式的家庭成员?还是受到伤害的亲戚?又或者是令人厌恶的入侵者?
num361-375
共92436
相关文摘
- 1. 奇遇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2. 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3. 索福克勒斯悲剧集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4. 形理两全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5. 大卫·霍克尼谈大卫·霍克尼:我的早年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6. Slash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7. 乱谈琴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8. 布莱希特,音乐与文化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9. 钢琴演奏之道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10. 毕加索与科克托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11. 缪斯之艺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12. 隐藏的潜能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13. The Shadow of the Sun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