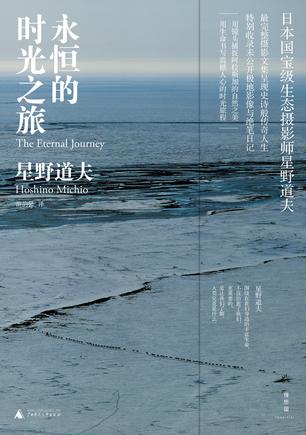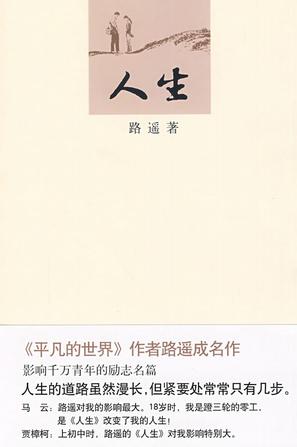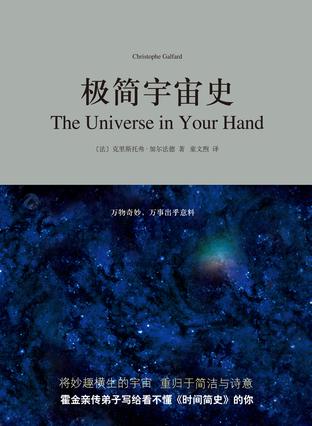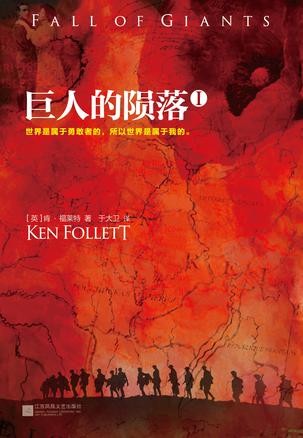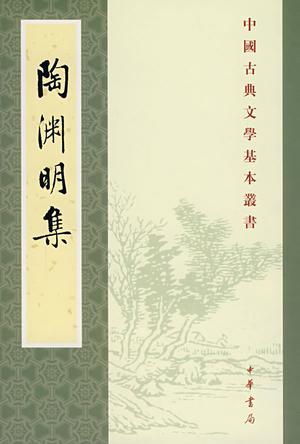-
“我要打破束缚人的枷锁—”她唱道。
-
“也许你的生活结束了,”她对他说,“但我的生活刚开始。也许我不再有你的爱了,如果我曾经有过——但至少我可以用钱买到任何东西,这就够了。”
-
我给人催眠,让他们穿过镜子,走出生活的这一面,进入生活的另一面。
-
“好斗的蚂蚁似乎对书不感兴趣。”他说,“但无论你在哪儿发现它们,你总能看到画。”他困惑地皱着眉头,“这真是蹊跷,彼特:画的爱好者从书的爱好者那儿进化而来。” “群居爱好者从个体爱好者那儿进化而来。”彼特若有所思地说,“那些有大螯的蚂蚁从没有螯的蚂蚁进化而来。”他休息一下眼睛,朝工具棚那儿看去,那儿有一张陈旧的宣传画,上面是斯大林的一双眼睛。
-
“等会儿和我们一起喝一口吧?”査理开玩笑地问。 “我很想,”内德说,“但我恐怕这个世界不配合。 “怎么了?” “我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内德说,“不过我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匆忙,所有人都匆匆忙忙,各自都怀着宏大的理想,千奇百怪,无所不有。也许,我们刚喝下去一口,正憧憬着过上完美的一天,就有人会冲进来,要么乱喊乱叫,要么胡作非为。”
-
“你看……”董事会主席说,“我曾经思考过像他这样的美国人会有什么下场。这些聪明能干的新人种,他们都认为活着就要让家里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富有,否则就算白来这个世界一趟。我经常琢磨着,要是经济形势恶化,要是这些聪明能干的人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身价跌了,”布里德先是指着地板,接着指着天花板,“而不是升了,他们会怎么办。” 现在,经济真的恶化了,自杀性流行病爆发前四个月就开始恶化了。 “这些都是只会走单行道的人。只能上不能下。”布里德说。 “他们的老婆和孩子也是只会走单行道,”艾弗雷特医生说,“我的天啊!”他走到窗口,看着哈特福德的冬景,“这个国家现在的主要行当,就是为了生活而献身。”
-
我经常碰到你这样的人,我知道,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有些人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识过外面的世界,也都没有经历过任何事情。
-
黛利小姐在办公室里坐着,兴奋得脸色粉红,呼吸急促。她正紧张地翻着文件,但是漫无目的,一无所获。她的嘴唇不停地动着,但什么声音也没有发出来。
-
“在美国钓鳟鱼”矮子的目光追随着她的背影,好像他们之间横亘着一条越来越宽的河流。
-
很多20年代的东西,很多车子、飞机、吸尘器、冰箱等等,都好像来自上个世纪末。是我们的速度之美使它们到了这个地步,使它们过早地衰老,衰老得如同上一个世纪的衣物和思想般。
-
我和外科医生聊了一小会儿,就相互告别。那天下午,我和家人要出发去爱达荷荒漠边缘的约瑟夫斯湖,而外科医生将出发去“美国”,那个时常只存在于他脑海中的地方。
-
巴塞罗那沦陷的时候,你和她飞到了英格兰,然后坐船回到了纽约。你们的爱留在了西班牙。那只是战争时期的爱情。你们在战争时期相爱,爱的其实只是自己。船行驶在大西洋上的时候,你们开始相互淡漠,一天一天失去了彼此。
-
十六岁的时候,先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然后是新奥尔良的妓女那里,他彻底明白了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
用人的名字给溪流命名的主意不错,将来的人们沿着溪流走一会儿,就能去了解那时的人们付出过什么,知道些什么,以及做成了什么。
-
我们也不能焚烧垃圾,因为那是旱季,所有东西都是易燃物,包括我们自己。
num85411-85425
共92389
相关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