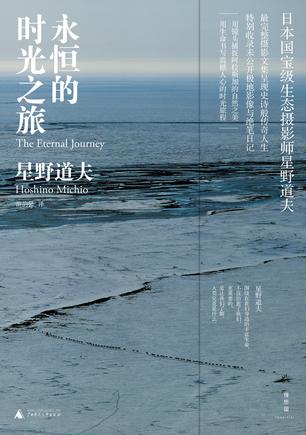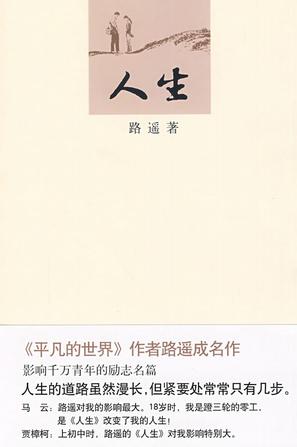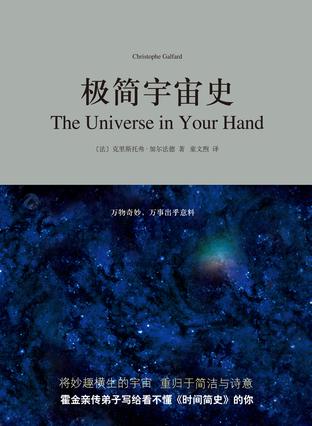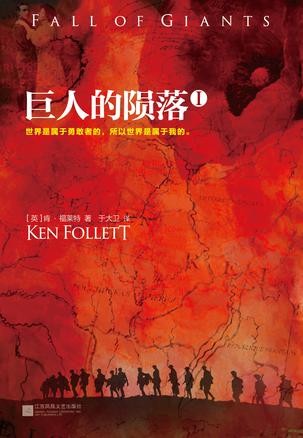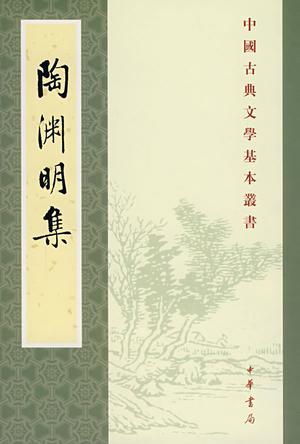-
他们瞪着死鱼似的眼睛,打着圈子回到原处:向北,向东,向南,向西,再向北。好人、穷人和善心人都感到没有一点希望。
-
空袭几天之后,警报声再一次响起。这一回从空中向心灵受创的不安的幸存者投下的是传单。我的那份“宏篇大论”现已丢失,但大致记得里面的内容:“德累斯顿的市民们:由于你们的铁路设施承担的大量军事运输任务,我们被迫轰炸你们的城市。我们意识到我们未能全部击中目标。任何除军事目标之外的损毁都并非有意,都是战争难以避免的不幸后果。”我相信,这样对大屠杀的解释会使每个人满意,但美国人投弹的精确度却让人难以恭维。事实上,最后一架B-17轰炸机轰鸣着朝西飞走去享受它应得的休息之后仅四十八小时,劳动队伍就涌入被毁坏的铁路道站,将它恢复到了几乎正常的工作状态。易北河上没有一座铁路桥梁被炸毁。投弹瞄准器生产商知道后应该感到脸红,因为他们神奇的仪器将炸弹导向了军方宣称为轰炸目标三英里以外的地方。
-
当这位高利贷者将他的库藏积累到历史最高点时,一个他一直急切地等待的大灾难让他香烟的价格直窜云端。
-
你能看得出来这四个一九一八年的小子,在弹坑里一圈一圈的爬,跟蜗牛在鱼缸里怕圈儿一样。每个人身后边都留着一道印子——活着的和死了的都这样。
-
在时间机器光束里,那感觉就跟得了流行感冒、戴上给别人配的眼镜和钻进吉他里面这三种加在一起。要是不改进改进,这玩意不安全,也没多少人会喜欢。
-
还有另一种说法:“他们自找的。不给点颜色他们永远不会明白。”谁自找的?谁看了颜色才会明白?
-
我们的任务是把你们变成世界历史上最卑鄙、最肮脏的一群斗士。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忘记昆士伯里的马奎斯准则,以及所有别的规则。可以用一切手段,不择手段。如果你能踢到对方皮带下方,就别去打他皮带以上的部位。让那个狗崽子哭喊。使用任何手段杀了他。杀,杀,杀,明白吗?
-
冯内古特小说的科幻色彩(代译后记) 将冯内古特( Kurt vonnegut,1922--2007)归入黑色幽默作家,应该没有疑义,作家本人也多半认同。他在去世前的最后一部品《没有国家的人》( 4 man without a country,2005)中说他自就喜欢讲一些滑稽有趣的事情,并发现开玩笑是聊天的一种好办法。而且他认为:幽默差不多是对恐惧的生理反应,大量的笑是由恐惧引起的。这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什么是黑色幽默。冯内古特说,对恐惧和灾难,有一种东西叫做没有笑声的玩笑,弗洛伊德称之“绞刑架上的幽默”。
-
法兹对自己小声说的只有一个词“乐园”。
-
我一一我在图书馆对智商作了研究,”塞尔玛说,“之后我在档案上査找,我发现我卡片上一个数字可能是我的智商“真有趣,”赫姆霍兹说,“多亏了你的谦虚。那个你认为是是雪商的数字,塞尔玛一是你的体重。你抬头看看我们,你所的只是谁重谁轻。拿我来说,你发现我曾经是个很胖的男孩。比弗洛伊德和我都不是天才,瘦小的施罗德也远非傻瓜。”
-
“...我眼下没有任何朋友,但我期待在纽约能找到几个朋友、在那儿,人们不担心人生短暂,不害怕面对生活真相。”
-
当他把午餐从托盘上转移到餐桌上,他给人的印象是,他饶有兴趣地遵循着自由落体定律——并不是因为他必须遵循,而是他认为这些定律好得要命。
-
他走到一面镜子前,用他的指关节敲了敲。"我一会儿就要穿过这面镜子。你们会看见我和我的镜像相遇、重合,收缩成针尖大小。随后这针尖大小的东西再度增长,不是我和我的镜像,而只是我的镜像。那时,你们会看见我的镜像慢慢离开你们,沿着长长的通道。看见那个我要远行的通道了吗?
-
她在那本书中叫塞莱斯特,是书的女主人公。她是一个不懂爱为何物的女人,直到她遇见了兰斯•马格南。当我见到她,她看起来彷彿又忘记了什么是爱。
-
至于女朋友----莱德,她们从来不是你以为的真正的朋友,要是你不爱她们,她们不会是你真正的朋友。要是你爱上了一个幽灵,她们也不会是你真正的朋友。
num85396-85410
共92389
相关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