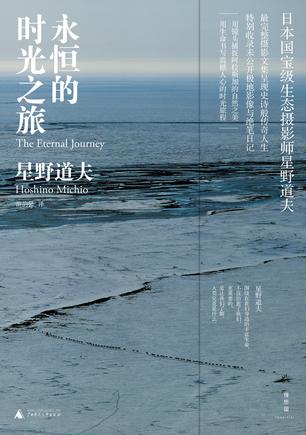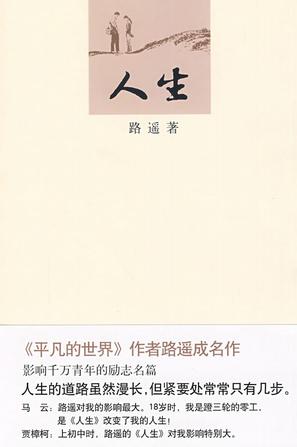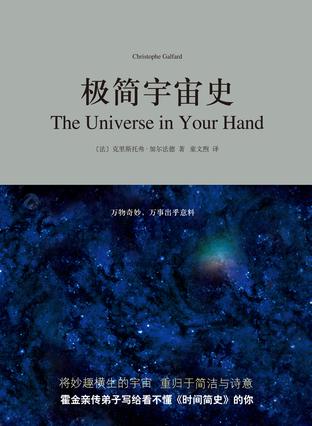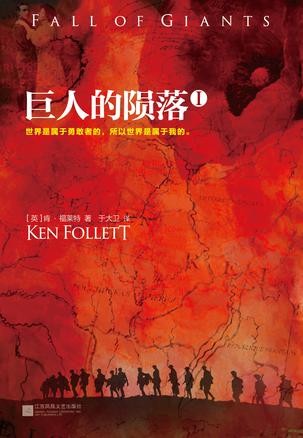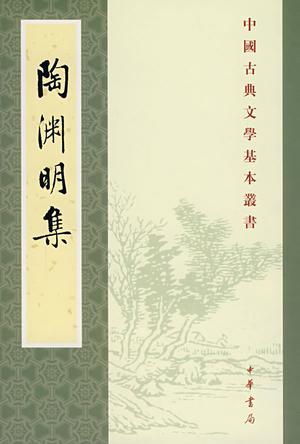-
她点了点头,不理会我的讶异,仿佛点头本身就是恶作剧的一部分。
-
罗马处处可见丘比特,因为我们剪下了他的一只翅膀,所以他不得不在空中盘旋。
-
当他为他的妻子、为我和为他自己倒酒时,我们俩终究会明白,他比任何时候的我都更像我自己,因为多年前在床上,在他成为我、我成为他之后,在人生的每条岔路上完成使命许久之后,他会是、也将永远是我的兄弟、我的朋友、我的父亲、我的儿子、我的丈夫、我的恋人和我自己。在那年夏天偶遇的几周,我们的人生几乎未受影响,可是我们却跨越到时间静止、天堂降临人间的彼岸,得到从降生以来神注定要赐给我们的那一份。我们望向一边。除了这件事,我们无所不谈。但我们始终知道,现在什么都不说却更确认了这一点。我们已经找到星星、你和我。而这是仅此一次的恩赐。
-
有些晚上,我把“大波浪”从袋子里拿出来,确认没沾染到塑料或我衣服的味道,然后抱着它,将两只长袖围在身上,在黑暗中低声呼唤他的名字。欧里法、欧里法、欧里法——那是奥利弗模仿马法尔达和安喀斯的古怪腔调,以他的名字呼唤我的声音;那也是我在以他的名字呼唤他,希望他也能以我的名字唤我的声音,我愿意代替他对我唤我的名字,再回应他:埃利奥、埃利奥、埃利奥。
-
或许是酒精,或许是真相,或许我不想把事情变抽象,总之我觉得我必须说出来,因为现在正是说这句话的时候。因为我明白这是我来这儿的原因,为了告诉他:“在我死去的时候,你是我唯一想要道别的人,因为唯有那时,我所谓的‘我的人生’才有意义。万一我听到你过世的消息,我所知道的自己的人生,还有这个此刻正在跟你说话的我,将不复存在。有时候我脑中会出现这样可怕的画面:我在我们 B城的家醒来,朝海的方向望去,听到海浪传来你已在昨晚过世的消息。我们错过了太多。那就是处于昏迷状态。明天我回到我的昏迷状态,你也回到你的昏迷状态。对不起,我无意冒犯——我相信你的人生里没有昏迷状态。”
-
他来得正是时候。没有一抹云彩,没有一圈涟漪,没有一丝风。“我都忘了我多爱这个地方了。但这里跟我记得的一模一样。中午的这里是天堂。”
-
我突然明白,我和他共度的是借来的时光,时间始终是借来的,而就在我们最无力偿还而且需要借得更多的时候,借贷机构却要强索额外费用。
-
我们随时就会道别。霎时,我生命的一部分就要被带走,再也不会归还。
-
这是我们的离别预演。仿佛看着一个插着呼吸机的人,而过两天就会被拔掉。
-
“就一会儿。不过我什么都不想做。”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再说吧,或许吧”的修正更新版。
-
我可能希望他明白,自从他上次来过之后,一切都没有改变,“天堂的门阶”依然在那儿,通往海边那扇歪斜的门依旧嘎吱作响,世界仍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只是少了维米尼、安喀斯和父亲。这是我想展现出的欢迎。但我也希望他意识到我们现在没必要叙旧。我们在少了彼此陪伴的状况下走过、也经历过太多,彼此已经没有任何共有的底色。或许我希望他感觉到失去的刺痛,以及悲伤。但到头来,或许经由妥协,我断定最简单的办法是表示我什么都没忘。
-
“那再让我讲一件事。这么做能够扫除我们之间的芥蒂。我或许曾经很接近,却从来没拥有过你所拥有的。总是有什么东西在制止或阻挠我。你怎么过日子是你自己的事。可是切记,我们的心灵和身体是绝无仅有的。许多人活得好像自己有两个人生,一个是模型,另一个是成品,甚至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种版本。但你只有一个人生,而在你终于领悟以前,你的心已经疲倦了。至于你的身体,总有一天没有人要再看它,更没有人愿意接近。现在的我觉得很遗憾。我不羡慕痛苦本身。但我羡慕你会痛。”
-
未来的那两人永远无法抹除、撤销、忘却或重温过去——过去就困在过去,像夏日黄昏将近时原野上的萤火虫,不断在说:你原本可以如此。但回头是错。向前是错。看开是错。努力纠正所有的错,结果同样是错。
-
我倾向于一种信念,那就是,生活有时足够仁慈,能够给予我们有效的隐喻来帮助我们看清自己是谁,渴望什么,又要去往何方。可是隐喻是一回事,生活又是另一回事。
-
可是相反,我把细微事物收集起来,好在未来贫瘠的日子里,让过去的微光带给我温暖。我开始不情愿地从当下窃取事物,好偿付未来将背负的债务。
num83071-83085
共92389
相关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