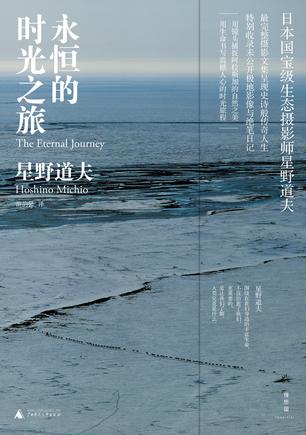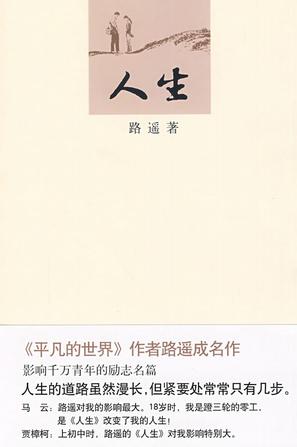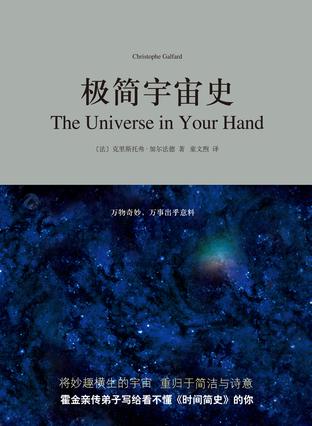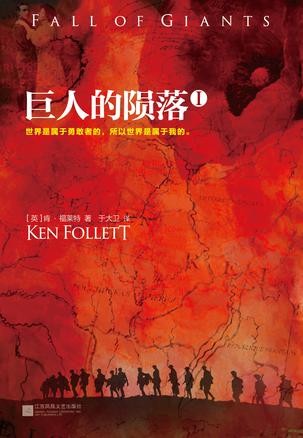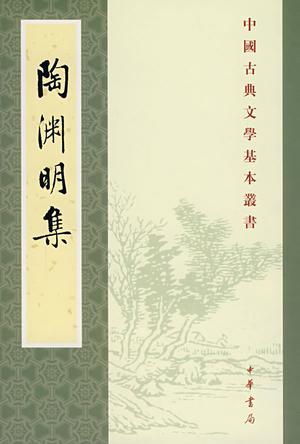-
我应该学着回避他,切断每个联系,一个接一个,像神经外科医生将一个神经元和另一个分开那样,不再许下那些自我折磨的心愿。
-
或者,我可能对于这一切要往何处发展,看得不够明白,宁可让事情不知不觉过去。再度沉默。直到他下次开口。
-
这念头就像舒爽的乳液,首先对你的四肢起作用,然后渗透到你身体的其他部分。它会提供给你各种论点,或支持,或反对,起初都是些幼稚说法,例如“今晚做什么都已太晚啦”之类的,然后上升至一些稍严肃的想法,比如“你如何面对他人,你就如何面对自己”。
-
但热情容许我们将更多东西隐藏起来,那一刻在莫奈的崖径上,我想把关于我的一切隐藏在这个吻里,我也渴望自己迷失在这个吻里,就像一个人希望脚下的大地裂开,然后将自己完全吞没。
-
“喜欢看书的人善于隐藏自我。隐藏自我的人未必喜欢自己。”
-
然而,下一次偶然碰到他,我只想对他表达感谢。我在表达感谢的同时,能否不令人觉得困扰或有负担?还是说,只要是“感谢”,无论多么克制,总带有丝丝多余的甜腻,让地中海式热情难免显得多愁善感又矫揉造作?不能适可而止,不能低调,一定要大肆声张,昭告天下,慷慨陈词。
-
在我有机会故意拉大我们之间的距离前,我感觉自己就像被花店临街橱窗上流动的水冲洗过一样,所有的害羞与压抑都被带走了。无论紧张与否,我已经懒得盘问自己的每一个冲动。如果我蠢,就让我蠢到底吧。如果我碰到了他的膝盖,那就碰着吧。如果我想拥抱,那就拥抱吧。
-
但现在我仿佛置身天堂。因为他没忘记我们有关策兰的对话,这让我前所未有地狂喜了好几天。
-
年轻如我,也知道这不会持久,我至少应该享受当下,而不是一再地用古怪的方式去试图巩固我们的友谊,或将之提升到另一个层次,结果搞砸一切。没有什么所谓的友谊,那没意义,只是一时的恩宠。
-
不把我不顾一切渴望给予的东西给他,或许是我这辈子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
-
我忘记在那个许诺里加的注是:冰霜和冷淡有的是办法,能立即撤销所有在晴朗日子签署的休战书。
-
我耸耸肩,表示不把敷衍的感谢当一回事。或许我只是希望他再说一次。
-
下山途中,经过“我的天地”,这次换我故意望向一边,仿佛我早已把那件事抛诸脑后。我相信如果当时我看他,我们会交换同样有感染力的微笑,那种提起雪莱之死时立刻从脸上抹掉的微笑。我们的距离可能因此拉近,只要提醒我们此刻需要保持多远的距离。或许故意望向一边并且清楚我们是为了避免“说话”才望向一边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找到相视而笑的理由,因为我确信他知道,我了解他明白我在避免提到莫奈的崖径,也确信这种无不透露着分离的回避,反而成了我们完美同步的亲密时刻,谁都不希望会消散。
-
我几次试着学他那样出门,可是我太沉浸于自我的感觉里了,像一个光着身子在更衣室走动的人原是想让自己更加自然,到头来却被自己的裸体勾起了性欲。
-
当晚在日记里,我写道:我说我认为你讨厌那部作品,是夸张了点。我真正想说的是:我认为你讨厌我。我希望你说服我,事实正好相反,你也的确这么做了一下。但为什么我明天早上就会不再相信?
num83116-83130
共92389
相关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