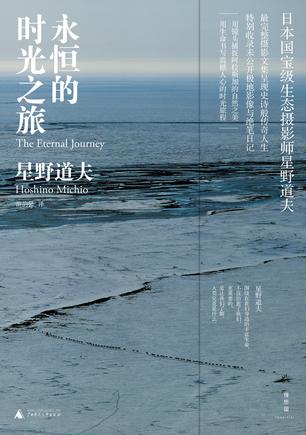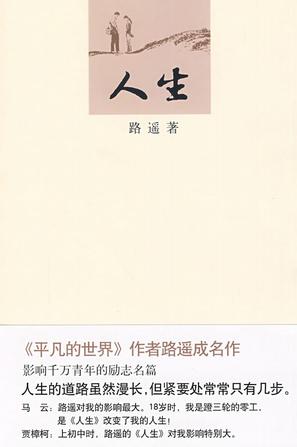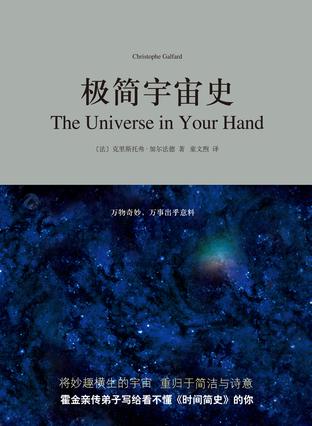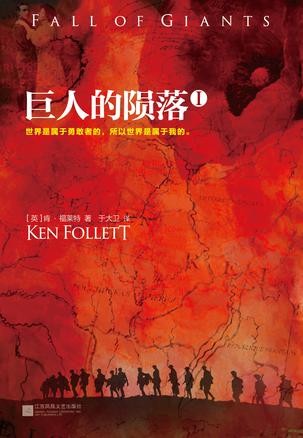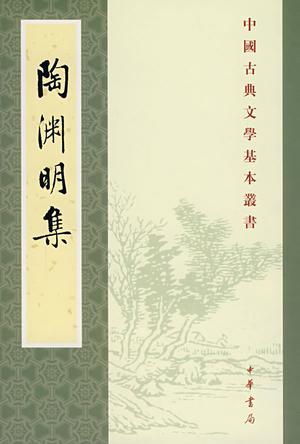-
把吸管像扔飞镖一样插进去。
-
或许看他和别人这样跳舞,让我明白他已有所属,就没有理由再抱希望。这是好事,可以帮助我复原。或许这么想已经是复原的前兆。我曾试图偷食禁果,现在却得到从轻发落。
-
“不会啊。”我回答。但对于一个诚心发问的人来说,我回答得太快了。为了减轻“不会啊”的含糊性,我又说我今天可能要睡一整天。“我觉得我今天没法去骑车了。”
-
此举刺痛了我。
-
如果心神不宁带来的失落感越积越多,那么一个人是否能够带着宽恕与慈悲,学着寻找将其视为常态的方式?
-
“你说话的时候看着他,他却总是撇开目光,没专心聆听,他只想趁忘记以前,赶紧说出你发言时他在心里演练过的话。”
-
拒绝大家普遍认可的,只会让他们察觉到,我实则隐瞒了需要抗拒他的真实想法。
-
就像是从一团可怕的梦魇中缓慢降落,但还没有完全着陆,也不确定是否想要着陆,因为尽管我知道自己无法继续与那团巨大又奇形怪状的梦魇相抗衡,而且那团梦魇仿佛是曾飘进我生命里的自我厌弃和自责之云中最大的一朵,但是降落之后等待着我的一切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
新欢的痛苦、郁热和震颤,眼看就能获得的美满幸福,却仍在咫尺之外徘徊;在他身边总是坐立不安,怕领会错他意思,担心失去他,遇事都要揣测再三;想要他也想被他要,使出各种诡计;架起重重纱窗,仿佛自己与世界之间立着不止一层的纸拉门;急吼吼地把本来就不算事的事儿煞有介事鼓捣一番后又装作若无其事——这些症状,在奥利弗来到我家的那个夏天,全都发生了。
-
但我也知道,如果他今晚出现,那么即将发生的事,无论是什么,即使一开始不合我的意,我也会让自己去经历,直到最后。
-
我敲了敲玻璃窗,轻轻地。我的心狂跳。我什么都不怕,那为何如此慌乱?为何?因为一切都令我害怕,因为恐惧和欲望都忙着对彼此、对我躲躲闪闪,我甚至无法辨别“想要他开门”和“希望他爽约”之间有什么不同。
-
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段误入 traviamento的时期,比方说,当我们转变人生方向或选择另一条路的时候。但丁就是这样。有些人知错能改,有些人假装反省,有些人一去不复返,有些人甚至还没开始就退缩,还有一些人因为害怕任何改变,最后才发现自己度过了错误的一生。
-
我刻意不去计算时间。起初是因为我不愿意去想他会和我们相处多久,后来则是因为我不想面对他在这里的日子越来越少。
-
就连没那么精明的人类灵魂观察者,也能在我的执意否认中,看出我只是拿基娅拉当幌子。
-
“你来这里做什么?”他一看到我就说。他用玩笑来隐藏自己并试图掩饰我们已经完全不交谈的事实。低劣的伎俩,我想。
num83131-83145
共92389
相关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