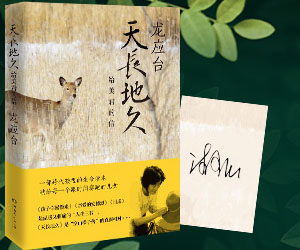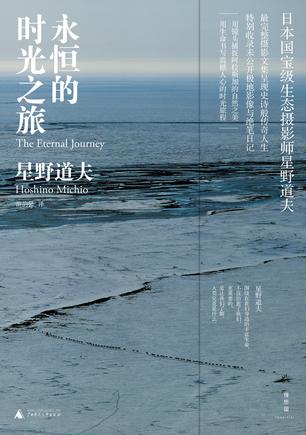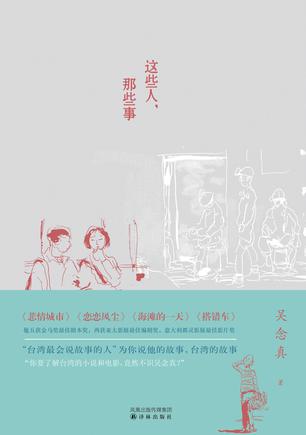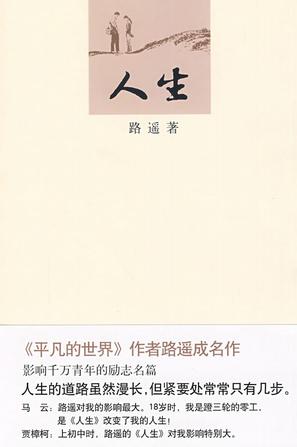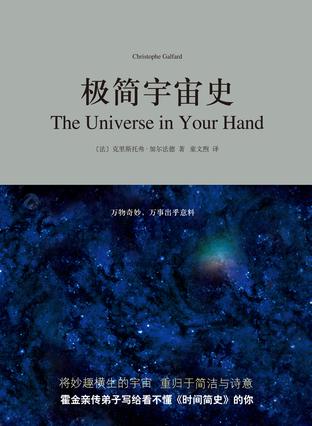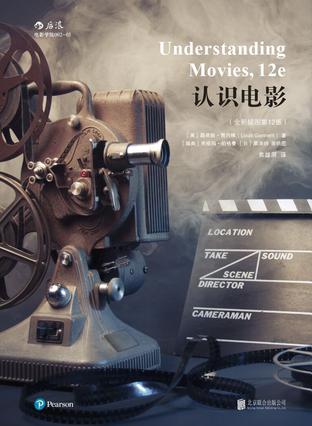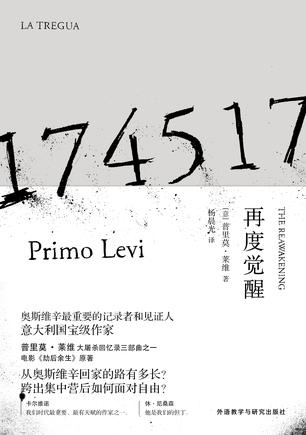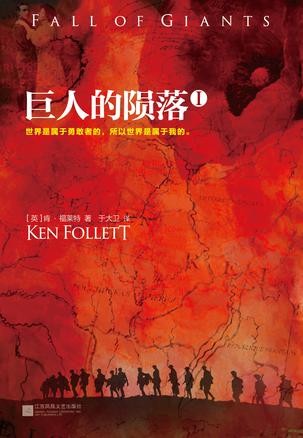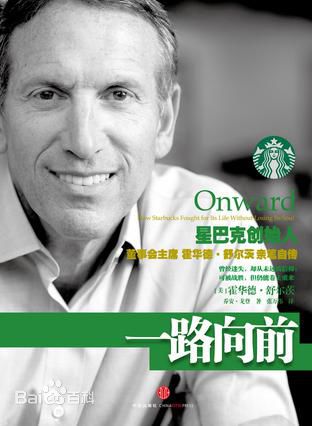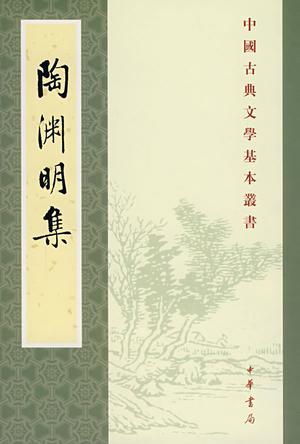-
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
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
-
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 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
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政治家?二十五年前,翰林院修撰徐时行(当时他尚未姓申,仍袭用外祖徐姓)也曾对这些问题发生疑惑。但是今天的大学士申时行对此早已涣然冰释,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妙,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
这一帝国既无崇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
-
传统的**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
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
恻动人,情节也真实可信。
-
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 的自我牺牲,贤委的茹苦含辛,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无数的条文和墓碑,可为例证。 这些文章多有出自儿子或丈夫的手笔,其中歌颂母亲或妻子给他们的赞助扶持,文句悱
-
万历的看法是,邹元标和其他诤谏者并非对他尽忠,而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这些人把正直当做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做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lizhigushi.com]。
-
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
-
在抗倭**中功绩最为卓着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
-
因为所谓“自己”,不过是一种观念,不能作为一种物质,可以囤积保存。生命的意义,也无非是用来表示对他人的关心。只有做到这一点,它才有永久的价值。这种理想与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的教义相近。印度的思想家认为“自己”是一种幻影,真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只有无数的因果循环。儒家的学说指出,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和外界接触,离开了这接触,这个人就等于一张白纸。在接触中间,他可能表现自私,也可能去绝自私而克臻于仁。
-
帝国的官僚**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成千成万的官僚,在维护成宪的名义下保持各方面的平衡,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利。
-
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又在社会风气中得到反外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入仕途,则极少有机 会表现他的特长,发挥他的创造能力;也极少有机会带给一家、一族以荣誉。所以一个
num82426-82440
共92389
相关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