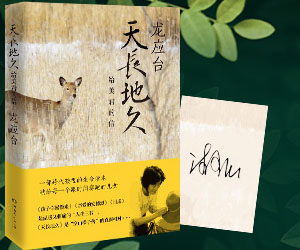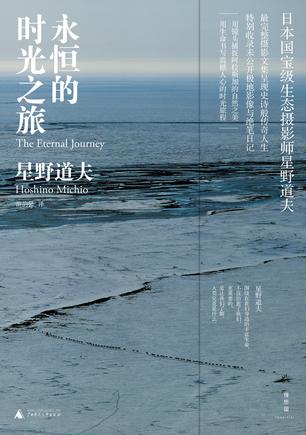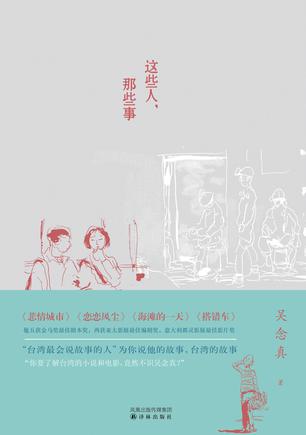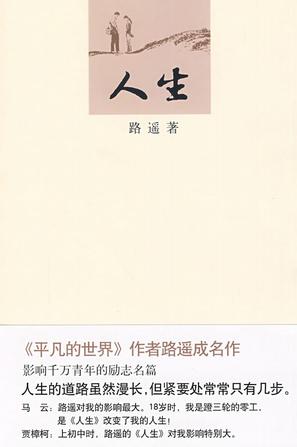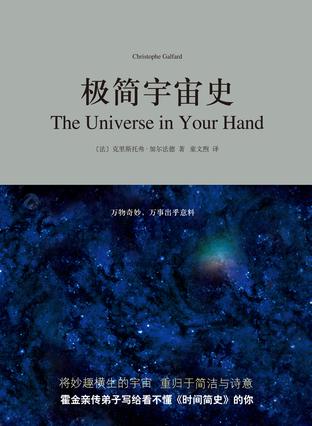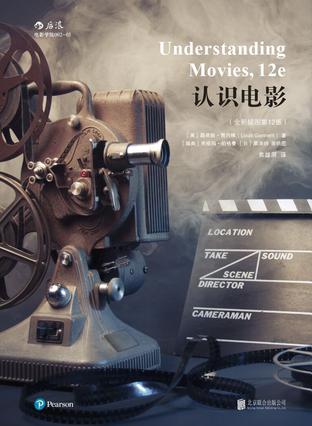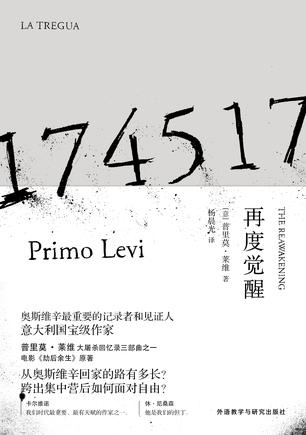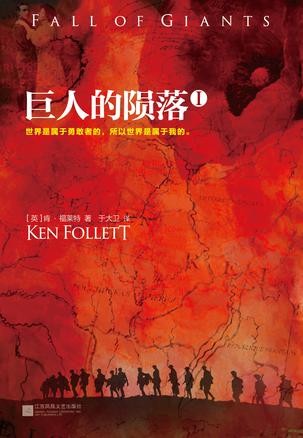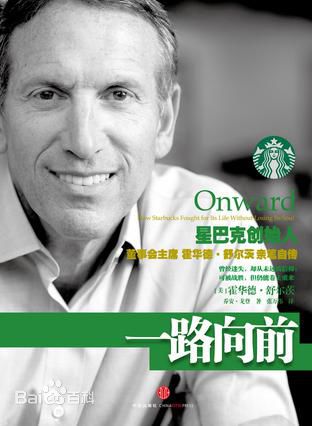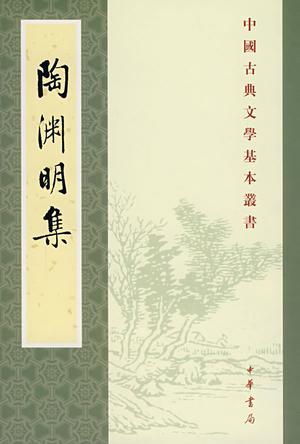-
日本美的特质,即在于大胆引入外来的异质文化,并将其同化于传统风土培育出来的民族美意识之中。
-
日本无保留地吸收外来文化,喜欢模仿,同时,又顽强地保持自我,由此产生刺激和紧张,生发出新的动力。在岛国这个闭塞之壶中,很早便成为统一之国家的日本,从未丧失过民族精神的基础,而且,借助外来文化的注入来防止自身的老化。
-
写在画面上的“杨・凡・爱克在此”的拉丁文,一般来说是画家的署名但在中世纪留下画家姓名的画是极少的,几乎见不到。只有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署名的风气才渐渐盛行起来。这是因为人们开始注意到画家的个性,同时画家也想明确表达自己的见解。这表明中世纪默默无闻的画匠们渐渐变成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家了。
-
不善于说理的人不必勉强译理论书, 不会作诗的人千万不要译诗,弄得不仅诗意全无,连散文也不像,用哈哈镜介绍作品,无异自甘做文艺的罪人。
-
藩擅称诏从单于求地,法当死,更大赦二,今徙藩为济南太守,不令当匈奴
-
如淳曰:“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漢官》曰大射于曲臺。”晉灼曰:“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也。”
-
“由於眼睛捕捉影像的速度遠比動手繪圖更為快速,因此,圖像複製的過程便大大加速,而得以跟上人們說話的速度。在攝影棚裡,攝影師便以演員說話的速度攝錄影像。如果說,平版印刷讓報紙可以附上插圖,那麼,照相術便預示著有聲電影的到來──人們在十九世紀末又發明了複製聲音的技術,也就是錄音技術。”
-
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并不能预先就决定一切。环境并非无所不能,但是它会对任何既定地点先天具备的或后天获得的有利条件产生很大的影响。
-
历史往往无公正可言,有些人注定是永远的发言人,另一些人则注定是永远的听众,注定要被埋没。但是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有权选择是站在历史一边还是相反,有权选择述说历史的角度和方式。
-
郭路生在大家熟悉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中写道:
-
而她完完整整地站在那里,看起来就跟刚开始一模一样,能做出同样的动作,拥有同样的名字,同样的习惯,同样的历史,没有更多。然而,从块状物中释放出来之后,她和所有不属于她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全都改变了。一种确定无疑但看不见的改变。现在,她成了周遭一切事物的核心。所有不属于她的东西都为她创造了空间。
-
当被某人如此热切地渴望着,而这渴望又是彼此相应时,会让被渴望的人无所畏惧。 被某人渴望着,或许会是任何人在活着的时候,感觉最接近不朽的时刻。
-
从本体论出发,文化艺术内部的演变有其相对的独立性,金石入书入画可以被看做是艺术的内部问题,然而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商人和市民阶层人数的增多,却从外部因素上制约和引导着书画家的创作,尤其是,19世纪末期的国家形势在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或者士大夫看来都是危机深重的。
-
多少年后(1992年),被徐悲鸿认为具有绘画天赋的家开创性努力的画家蔡亮说过这样的话: 中国的艺术家恐怕没有什么特殊的艺术观点,他离不开党的政策所规定的那样一些文艺原则,即使有一点自己的这样的看法、那样的看法,那都不见得能成一个什么体系的东西。如果一定要说什么观点的话,那就是凭良心千活。
-
但不满更深的根源在于孤独,在于一种隔离感,在于毁坏只有同质的、结合紧密的社会才能给予其成员的那种团结。
num57676-57690
共90354
相关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