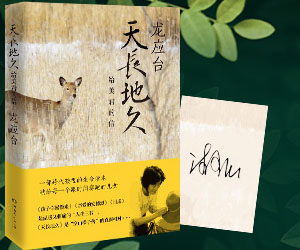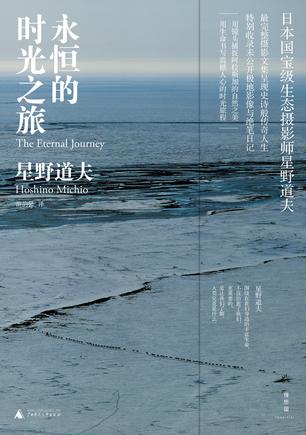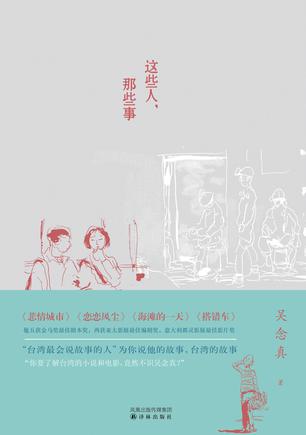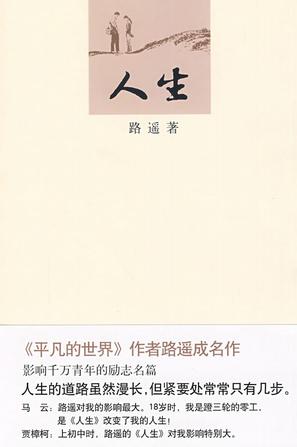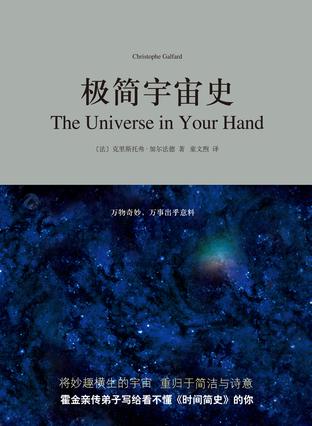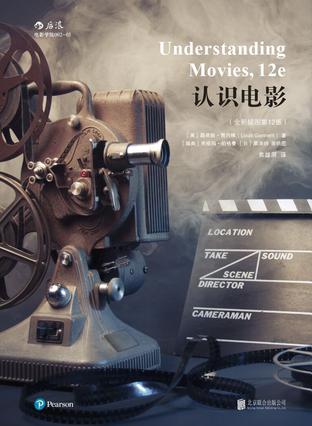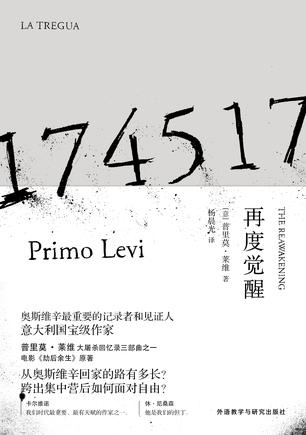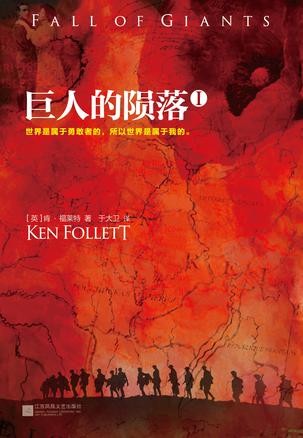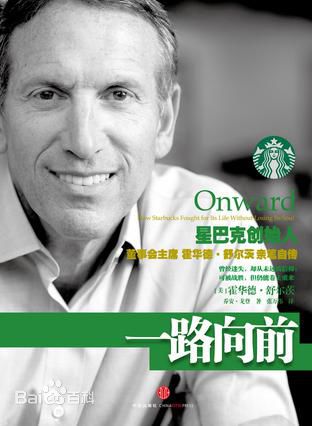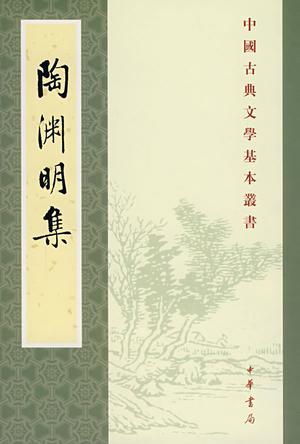-
因为人与生俱来就有两种愿望:一种是自由的愿望,一种是安全的 愿望。人的天性决定了人存在有拿自由换安全的可能。 公平与否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感觉。我们讲的"公平"并不是指 分配的"平均性"或"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问题,而是一个权利义务的对等
-
社会源于我们的欲望,而政府来自我们的邪恶。 任何事物越是简单,便越不容易发生紊乱,并且即使发生紊乱也比较容易加以补救。
-
加之前章曾提到的,生活模式与生活周期的均质同一化正是工业社会的特点所在。18岁或22岁都在学校读书,之后就职,30岁之前结婚,生两个孩子,贷款买房……几乎所有人都是如此。
-
尽管牧师首先感兴趣的是在产业工人和雇员之中宣传基督教信条,但他们在工厂的体验打开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从个人精神修炼的空洞性中走出来,看到了工人进行集体斗争改善工厂条件的必要性。
-
当我们从什么是对繁荣最有利的因素转到什么是对繁荣最不利的因素时,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当存在激励因素促使人们去攫取而不是创造,也就是从掠夺而不是从生产或者互为有利的行为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时候,那么社会就会陷入低谷。
-
在一个绝对主义统治的政权下,如果存在谁可能是下任统治者的共识,那么这对所有人都是有好处的。即使在当代也是如此,因为这不仅会减少围绕继承问题的战争,也会增加经济信心以及投资、收入和税收所得。
-
但我们能够合理地期望社会主义社会可容忍的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社会在周期阶段平均产生的投资率。即使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也不足以产生足够的投资率,它必须得到公司积累和“创造的”银行信用的增援,这些方法既不是特别自动的,也不是独特决定的。
-
不同时期和不同著者把为“忠臣”、“义士”们保留的财产称为“国库财产”、“恩赏”、“荣赏”、“采地”。
-
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作者笔下,为这些家臣保留的财产分别被叫做国库财产、恩赐、荣赏、采地。
-
自然,他们每个群体都发展出了潜规则都能从中得到实惠。(前言)
-
罗马的力量是圣保罗所谓的那种“阻遏性力量”——阻遏完全失序的状态或者基督教谓为敌基督统治的无政府状态。
-
“万事不可过分”,自荷马时代以来,这就是希腊伦理的最主要原则。在被亚里士多德(正如早得多的梭伦一样)应用于政体形式之后,这一信念成了亚里士多德及其学派在秩序观上的主要贡献。其表现载体便是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观[有时被称为“黄金中点(Golden Mean”)。
-
天人灾异之说......犹据以劝戒时君......然而时君不信,徒为避殿罪己之具文。甚至每逢灾变,“切让三公”,比之告朔饩羊,更为无益而有害。盖士大夫欲正君匡政,操术犹故,而作法自毙,以矛陷盾,反为奸邪所乘矣。
-
专制时代之君臣,虽推尊孔子,表章儒术。其实断章取义,别具私心,存其仁义之言辞,略其封建之背景,忘其平阶级之宗旨,遗其君子儒之教义。
-
天人灾异之说......犹据以劝戒时君......然而时君不信,徒为避殿罪己之具文。甚至每逢灾变,“切让三公”,比之告朔饩羊,更为无益而有害。盖士大夫欲正君匡政,操术犹故,而作法自毙,以矛陷盾,反为奸邪所乘矣。
num59461-59475
共90452
相关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