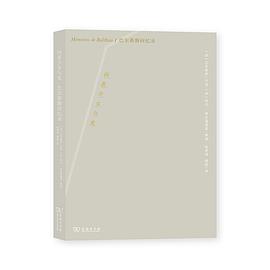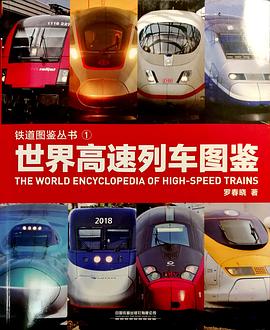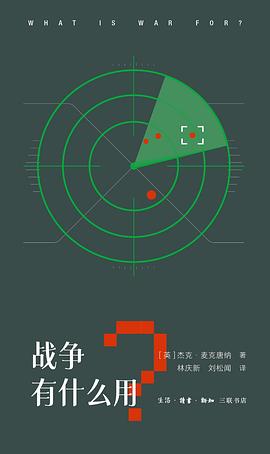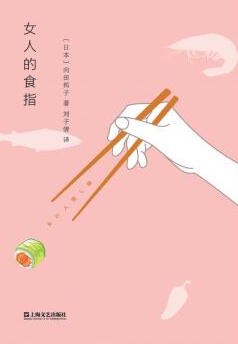内容简介
《无可慰藉》是石黑一雄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一部极尽绵密细腻、令人难以自拔的心理小说奇作。本书秉承石黒一雄的一贯风格,外表清淡,内心强大。小说描写一位钢琴演奏家在一座谜样的城市里所经历的谜样的几天。他忽而是旁观者,忽而又被卷入其中,所见之人无不一往情深却又执迷不悟;所遇之事无不怪异荒诞,充满变数。在这座人心为怪诞的艺术价值观所左右的城市里,在努力寻找梦境出口,为这一切寻求解释的过程中,他渐渐意识到自己正面临人生最为严酷的一场演奏。
双语版《无可慰藉》附上作品原文,可以令读者同时欣赏到石黑一雄精妙优美的英文原文,得到双重美的享受。
......(更多)
作者简介
石黑一雄,日裔英国小说家,1954年生于日本长崎,与奈保尔、拉什迪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石黑一雄的作品并不多,但几乎每部作品都获得重要的文学奖项:《远山淡影》获温尼弗雷德•霍尔比纪念奖,《浮世画家》获惠特布莱德年度最佳小说奖,《长日将尽》获布克奖,《无可慰藉》获切尔特纳姆文学艺术奖,《浮世画家》《我辈孤雏》和《莫失莫忘》均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1995年英女王授予石黑一雄文学领域的大英帝国勋章,1998年获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2017年因“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发掘了隐藏在我们与世界的虚幻联系之下的深渊”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更多)
目录
......(更多)
读书文摘
I forced what remained of the cake into my mouth and brushed the crumbs from my hands.
如同小说中的瑞德及其他所有人一样,行走在当代社会,我们的心灵全都带着自己的伤口,被困在各自形形色色的大泡泡中,无法与人沟通,也无法从外界获得帮助和慰藉。
沉默很可能意味着最深远思想的形成,最深处能量的召唤。
想当初,我那时是有过些计划,就像您年轻时那样,在您还不知时间是多么有限的时候,您还不知您四周已建起了一个壳的时候,一具硬硬的外壳,您根本出――不――去!
您知道老人有时做梦的方式,他们心想,假如自己在某些关键时刻选择了另一条路,生活又会怎样。呃,一个城市,一个社会,也会如此啊――不时地回望过去,回想历史,扪心自问:“会怎样呢?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假如我们当初只要……”
事情也许由不得你,没必要弓肩缩背啊。
狭窄的世界!你生活的世界太狭窄!
哦?你怎么知道我不懂?我可能很有科学头脑呢。你不应该这么快对一个人下结论,鲍里斯。
这些人把你打扮得像个木偶,而你竟然随他们那么做。
听着,我只是没有按你的那种方式生活而已!
身处一个科技爆炸、沟通无限的世界,我们感受到的,却是史无前例的孤独无助。在全世界都可以社交起来的时候,我们却无法用最原始的方式获得真正有效的沟通
我曾喜欢那感觉,按压伤口的感觉,它让我着迷。一个真正的伤口,就有那样的作用,会让人着迷。每天看起来都会有些不同。你便会想,变了吗?或许最终会痊愈吧。你望着镜中的它,好像是不同了。但是,当你触碰它时,你知道还是副老样子,还是你的老朋友。
这是另一种很常见的失败。相信把东西放在文件夹里就会变成事实!
一个伤口,就变得像个老朋友一样。当然,它时不时会烦烦你,但我已经与它生活了这么久。
太晚了。我们已经失去它了。为什么我们不听天由命,就随它变成另一个冰冷的、孤独的城市呢?其他城市已经是这样了。至少我们还会顺应潮流。这座城市的灵魂,不是病了,瑞德先生,而是死了。现在太迟了。
听着,你们适可而止吧!停下这……这愚蠢无比的闲聊,哪怕就一会儿!就停一小会儿,让其他人,让外面世界来的其他人说说话,你们在这个封闭的小世界里全都住得太快活了!
我认为人的一生中总会有某个时刻,需要坚守自己的决定。一个说“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选择”的时刻。
“你要是想,可以把我扔出去啊,”鲁班斯基医生说道,开始吃起土豆泥来。“但看上去好像――”他拿着汤勺在屋子里挥动了一圈,“好像这儿并不是每个人都不想我来。要不我们来投个票吧。如果我真的不受欢迎,那我很乐意离开。举手表决,怎么样?”
窗外,太阳越升越高,照亮了一条条街道和我们这一边的车厢。只有当我们把能吃下的都吃了,把可能聊的都聊了之后电工可能才会看一眼手表,叹口气说,我酒店的那一站绕了一圈又要到了。我也叹了口气,不情不愿地站起身,掸了掸大腿上的面包屑。我们会握手,互道日安――他也会告诉我,他马上也得下车了――然后我离开,加入到围聚在下车处的那群兴高采烈的乘客中。接着,电车停靠,我也许会向电工最后挥挥手,然后下车,确信我可以很自信骄傲地期盼赫尔辛基之行。
我们每人都能详述十来个悲伤的案例:孤独寂寞的生活;好多家庭对曾经视为理所当然的幸福深感绝望。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