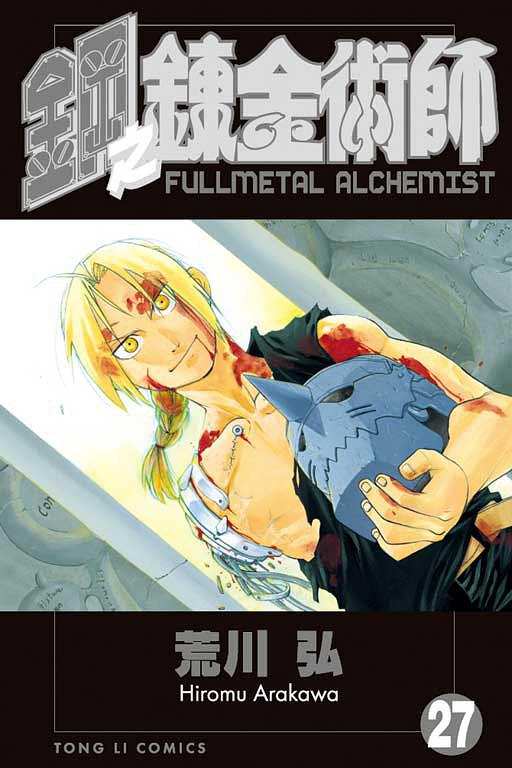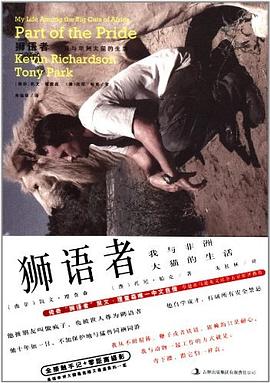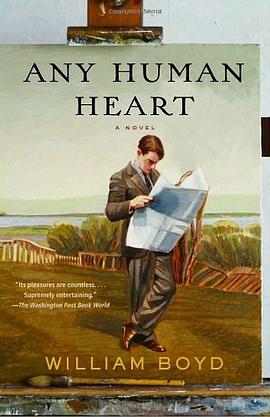内容简介
此书有三部分构成:《译本序》(施咸荣)、《麦田里的守望者》正文、《一部作品的出版史》(董鼎山)。
英国《卫报》根据书店销量研究公司的资料,列出英国人最喜爱的20世纪20本经典小说,结果荣登榜首的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是一本可以让人一口气读完而掩卷沉思的书,被《时代周刊》称为"现代文学十大经典之一"。
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个中产阶级子弟的苦闷、彷徨的精神世界,真实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精神文明的实质。全文都是以一个青年的口吻进行叙述,让人读来亲切感人而真实。
《麦田里的守望者》虽然只有十几万字,它却在美国社会中和文学界产生过巨大影响。小说一问世,立即引起轰动,特别受到大中学生的热烈欢迎。他们纷纷模仿主人公霍尔顿的装束打扮,讲"霍尔顿式"的语言,因为这部小说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反映了他们的理想、苦闷和愿望。
塞林格这本薄薄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影响了几代美国青年,大概也影响了不止一代中国青年。
这本在世界文学中也算得上"现代经典"之作,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这个译本的出现以来,已有多种版本多次印刷,常销不衰。
......(更多)
作者简介
作者塞林格全名杰罗姆・大卫・塞林格,一九一九年生于美国纽约城,父亲是做于酪和火腿进口生意的犹太商人,家境相当富裕。塞林格十五岁的时候,被父母送到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军事学校里住读,据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关于寄宿学校的描写,很大部分是以那所学校为背景的。一九三六年,塞林格在军事学校毕业,取得了他毕生唯一的一张文凭。
从一九四○年在《小说》杂志上发表他的头一个短篇小说起,到一九五一年出版他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止,在十余年中他共发表了二十多个短篇,有些短篇还在《老爷》、《纽约人》等著名刊物上发表,从而使他在文学界有了一点点名气。成名后他隐居到乡下,特地为自己造了一个只有一扇天窗的水泥斗室作书房,每天早晨八点半就带了饭盒入内写作,直到下午五点半才出来,家里任何人都不准进去打扰他;如有要事,只能用电话联系。他写作的过程据说还十分艰苦,从《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后,他写作的进度越来越慢,十年只出版三个中篇和一个短篇,后来甚至不再发表作品。偶尔有幸见过他的人透露说,他脸上已“显出衰老的痕迹”。他业已完成的作品据说数量也很可观,只是他不肯拿出来发表。不少出版家都在打他的主意,甚至在计划如何等他死后去取得他全部著作的出版权,但至今除本书外,作者只出版过一个短篇集《九故事》(195)和两个中篇集《弗兰尼与卓埃》(1961)及《木匠们,把屋梁升高;西摩;一个介绍》(1963)。
......(更多)
目录
......(更多)
读书文摘
对一个人来说,一辈子里注定会不时去寻找一些他们自身周围所不能提供的东西,要么他们以为自身的周围无法提供,所以放弃了寻找,他们甚至在还没有真正开始寻找前,就放弃了。 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轰轰烈烈地死去,而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谦恭地活下去。
问题是我不喜欢这样,琢磨一下就会觉得这主意很馊。我觉得如果你并非真的喜欢一个女孩儿,就不该跟她瞎胡闹。真的喜欢她,就应该喜欢她的脸。如果你喜欢她的脸,就不应该对她的脸做出这种下流事,比方说往她脸上喷水
人生的确是场球赛,孩子。人生的确是场大家按照规则进行比赛的球赛。
不可能因为一个人死了,你就从此不再喜欢他,老天爷,尤其是那人比你认识的那些活人要好一千倍。
通常都是这样,你越是不想说话,对方却越是有兴头,越是想跟你展开讨论。
那是十二月,天气冷得象巫婆的**,尤其是在这混帐的小山顶上。
我不停在脑筋里想像很多小孩在麦田地什么的玩游戏。有几千个小孩,没别的—没别的大人,我是说,除我之外。我就站在这破悬崖边上,我要做的,就是捉住每一个跑向悬崖的孩子--我是说他们不看方向的话,我就得从哪出来把他们捉住。我就整天干这种事。我就当个麦田守望者得了吧。我晓得这很疯,但这是唯逐一件我想做的事了。我晓得这很疯。
有些事物应该老保持着老样子。你应该把它们搁进那种大玻璃柜里,别去动它们。我知道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不过这照样是件很糟糕的事。
我没做的唯一原因是我当时情绪不对头。要是没那种情绪,这类事是做不好的。
我想,你要是真不喜欢一个女人,那就干脆别跟她在一起厮混;你要是真喜欢她呢,就该喜欢她的脸,你要是喜欢她的脸,就应该小心爱护它,不应该对它干那种下流事,如往它上面喷水。真正糕的是,许多下流的事情有时候干起来却十分有趣。而女人们也好不了多少;如果你不想干太下流的事,如果你不想毁坏真正好的东西,她们反倒不乐意。
如果有人在做决定的时候征求你的意愿,那感觉是很不错的。但是了解到你的意愿之后却不加以考虑,那还不如不要问。
我是说他学问倒是真的有,可你看得出他没多少脑子。
真正的朋友,无论男女,若是相知,必然相惜,若真相惜,只为真心,无关风月。
她的心肠软得就跟他妈的狼差不离。那些在电影里看到什么假模假式的玩艺儿会把他们的混帐眼珠儿哭出来的人,他们十有九个在心底里都是卑鄙的杂种。
他口口声声跟我说,我要不喜欢那些门徒,也就是不喜欢耶稣本人。他说,既然耶稣选择了那些门徒,你就应该喜欢他们。我说,我也知道他选择了他们,不过他只是随便挑选的。我说,他没有时间对每个人作仔细研究。
当年轻的时候,可以选择为理想而崇高的死;当年长的时候,可以为理想而卑微的活。
千万别跟人说事,说了你就会想起每一个人。
学校教育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如果你接受学校教育相当长一段时间,它就开始让你对自己的心性如何有个认识,认识到什么适合自己的心性,还可能认识到什么不适合。
一个人不成熟的标志是为了一个理由而轰轰烈烈的去死。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为了一个理由谦恭的活下去。
你要是听我聊,首先想知道的,大概是我在哪儿出生,我的糟糕的童年是怎么过去的,我爸妈在我出生前干吗的,还有什么大卫·科波菲尔故事式的屁话,可是说实话,那些我他妈的都不想说。
我痛恨这类事情,我并不在乎悲伤的离别还是不痛快的离别。只要是离开一个地方,我总希望离开的时候自己心中有数,要不然,我心里就会更加难受。
不管怎样,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
我要定出这么个规则,凡是来看我的人,都不准在我家里做任何假模式的事。谁要是想在我家里作假,就马上请他上路。
你哪怕去十万次,那个爱斯基摩人依旧刚捉到两条鱼;那些鸟依旧往南飞;鹿依旧就在水洞边喝水,她们的角依然那么美丽,它们的腿依旧又细又好看;那个裸着乳房的印第安女人依旧在织同一条毯子。给也不会改变样儿。唯一变样的东西只有你自己。倒不一定是老什么的。严格来说,倒不一定是这个。
他妈的金钱。到头来它总会让你难过得要命。
遇到深夜有人在街上大笑,纽约确是个可怕的地方,你在好几英里外都听得见笑声,你会觉得那么孤独,那么沮丧
有些人老得快死了,就象老斯宾塞那样,可是买了条毯子却会高兴得要命。
我要赚钱建一个自己的小木屋,余生就在那里度过.....
你出生的时候,你哭着,周围的人笑着;你逝去的时候,你笑着,而周围的人在哭!
每个人都有潜在的能量,只是很容易:被习惯所掩盖,被时间所迷离,被惰性所消磨。
我也和你一样,一样的帽子,一样的衣服,一样的动作。可是哈克,你可以和我一样吗?在麦田自由的奔跑……
这类事情老让我笑疼肚皮,我老是在跟人说“见到你真高兴”,其实我见到他可一点也不高兴。你要是想在这世界上活下去,就得说这类话。
接着她把我介绍给那海军军官。他的名字叫鲍洛甫队长什么。他就是那种人,跟你握起手来要是不把你的指头捏断那么四十根,就会以为自己是娘儿腔。
就跟斯特拉德莱塔一样。所有这些漂亮家伙全都一个样儿。他们只要一梳完他们混帐的头发,就理都不理你,自顾自走了。
我住在纽约,当时不知怎的竟想起中央公园靠南边的那个小湖来了。我在琢磨,到我回家时候,湖里的水大概已经结冰了,要是结了冰,那些野鸭都到哪里去了呢?我一个劲儿琢磨,湖水冻严以后,那些野鸭到底上哪儿去了。我在琢磨是不是会有人开了辆卡车来,捉住它们送到动物园里去。或者竟是它们自己飞走了?
有时候我觉得你拿她们取笑以后,她们反倒高兴,事实上,我知道她们是会高兴的,可你一旦跟她们相处久了,平时从来没拿她们取笑过,那简直很难开始。
对一个人来说,一辈子里注定会不时去寻找一些他们自身周围所不能提供的东西,要么他们以为自身的周围无法提供,所以放弃了寻找,他们甚至在还没有真正开始寻找前,就放弃了。
一个尚未成熟的男子的标志是他甘愿为某种事业而英勇献身,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甘愿为某一事业卑微地生活
她是我生平遇到过的跳舞跳得最好的姑娘之一。我不开玩笑,有些极傻极傻的姑娘真能在舞池上把你迷住。那般真正聪明的姑娘不是有一半时间想在舞池上带着你跳,就是压根儿不会跳舞,你最好的办法是干脆留在桌上跟她痛饮一醉。
这听起来好象没什么,我知道,可你跟她握起手来却是滋昧无穷。大多数的姑娘你要是握住她们的手,她们那只混帐的手就会死在你的手里,要不然她们就觉得非把自己的手动个不停不可,好象生怕让你觉得腻烦似的。琴可不一样。我们进了一个混帐电影院什么的,就马上握起手来,直到电影演完才放开,既不改变手的位置,也不拿手大做文章。跟琴握手,你甚至都不会担心自己的手是不是在出汗。你只知道自已很快乐。你的确很快乐。
那么闲待着,实际上是想感受一下离别滋味。我是说,以前我也离开过一些学校还有地方,当时根本没感觉正在离开那儿,我不喜欢那样。不管那种离别是伤感的还是糟糕的,但是在离开一个地方时,我希望我明白我正在离开它。如果不明白,我甚至会更加难受。
别跟任何人说任何事。要是你说了,你就会开始想念所有人。
不管那种离别是伤感的还是糟糕的,但是在离开一个地方时,我希望我明白我正在离开它。如果不明白,我甚至会更加难受。
领我进房间的侍者是个六十五岁左右的老头子,他这人甚至比房间更叫人泄气。他正是那一类秃子,爱把所有的头发全都梳向一边,来遮掩自己的秃顶。要是我,就宁可露出秃顶,也不干这样的事。
也许有些人很可恶,有些人很卑鄙。而当我设身为他想象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比我还可怜。所以请原谅所有你见过的人,好人或者坏人。
你是不是认为每样东西都该有一定的时间和地点?你是不是认为要是有人跟你谈起他父亲的农庄,他就应该把这个问题谈完,随后在改换话题,谈他舅舅的支架?或者,他舅舅的支架既然是他那么感兴趣的题目,那么他一开头就应该选它做讲题,不应该选他父亲的农庄?
我没回答他,我只是起身走到窗口往外眺望,一霎时,我觉得寂寞极了,我简直希望自己已经死了。
接着他和老萨丽开始聊起他们两个都认识的许多熟人来。这是你一辈子从来没听到过的最假模假式的谈话。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不断想出一些地方来,然后再想出一些住在那地方的人,说出他们的名字。
我不喜欢他说话离题,更不喜欢他太不离题。
除非他们自己掌控场合排场,这些高智商的人都不想跟你举行高智商对话。
“看到你真高兴”其实看到你一点也不高兴,只是不说这话没办法在这世界上活下去。
快乐要有悲伤作陪,雨过应该就有天晴。如果雨后还是雨,如果忧伤之后还是忧伤。请让我们从容面对这离别之后的离别。微笑地去寻找一个不可能出现的你!
对某些人是球赛。你要是参加了实力雄厚的那一边,那倒可以说是场球赛,不错——我愿意承认这一点。可你要是参加了另外一边,一点实力也没有,那么还赛得了什么球?什么也赛不成。根本谈不上什么球赛。
千万不能和别人说事,说了你会想念每一个人,我甚至有点想莫里斯那个混蛋。
问题是,每当你要跟一个姑娘行事的时候——我是说不是个做**什么的姑娘——十有九次她总不住地叫你住手。我的问题是,每次我都住手了。大多数男人都不这样。我却由不得自己。你总拿不准她们是真正要你住手呢,还是她们害怕得要命,还是她们故意要你住手,万一你真的干了那事,那么过错就都在你身上,她们可以脱掉干系。
”我想有一天,“他说,”你得会找出你想要去的地方。随后你非开步走去不可。
有些人是不能开玩笑的,尽管他们有可笑的地方。
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你千万别跟任何人谈任何事情,只要你一谈起,就会想念起每一个人来。
你一定得认识到自己想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一定要对准那个方向出发,要马上。你再也浪费不起多一秒的时间了,你浪费不起。
快乐要有悲伤作陪,雨过应该就有天晴。假如雨后还是雨,假如忧伤之后还是忧伤.请让我们从容面对这离别之后的离别。微笑地去寻找一个不可能出现的你。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的守望者。我知道这有点异想天开,可我真正喜欢干的就是这个。
我们确实活得艰难,一要承受种种外部的压力,更要面对自己内心的困惑。在苦苦挣扎中,如果有人向你投以理解的目光,你会感到一种生命的暖意,或许仅有短暂的一瞥,就足以使我感奋不已。
我只知道我很想念我所谈到的每一个人。甚至老斯特拉德莱塔与阿克莱,比方说。我觉得我甚至也想念那个混帐毛里斯哩。说来好笑。你千万别跟任何人谈任何事情。你只要一谈起,就会想念起每一个人来。
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轰轰烈烈地死去,而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谦恭地活着。
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的守望者。我知道这有点异想天开,可我真正喜欢干的就是这个。
我将来要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有那么一群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玩。几千几万的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就是在那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是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做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我们确实活得艰难,一要承受种种外部的压力,更要面对自己内心的困惑。在苦苦挣扎中,如果有人向你投以理解的目光,你会感到一种生命的暖意,或许仅有短暂的一瞥,就足以使我感奋不已。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