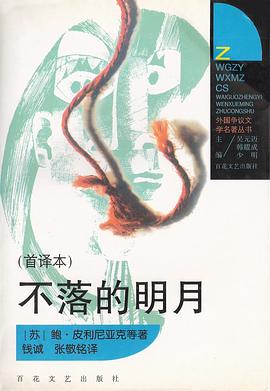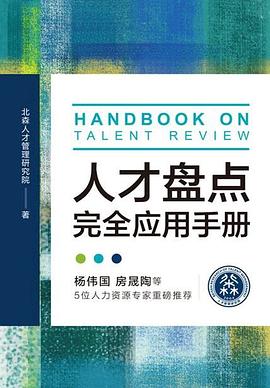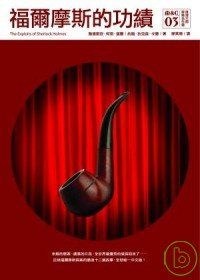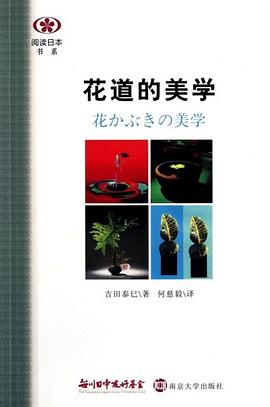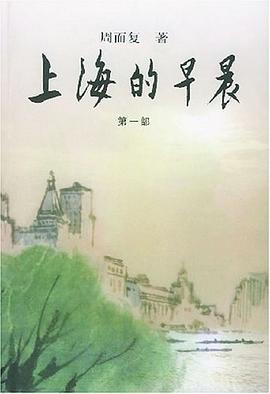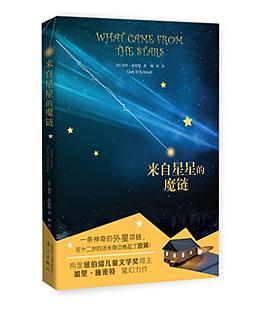不落的明月
内容简介
本书选收苏联开禁的三部曾有过争议的小说,其中前两部被禁锢长达六十余年之久,后一部也被湮没了有二十五个春秋。然而,它们一旦开禁,拭去历史尘埃,愈加显得光彩夺目。
《不落的明月》系苏联俄罗斯作家鲍•皮利尼亚克的代表作之一。三十年代曾轰动一时,引起过轩然大波。小说真实可信地披露了苏联红军高级将领伏龙芝猝死的疑案,并揭示了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源。作品渗透着作者的坚定信念,哲学思考和给读者的启示。
才华横溢的苏联俄罗斯作家米•布尔加科夫所著的《狗心》,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极富哲理探索的讽剌性作品,是作者以怪诞幻想的手法提出的对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思考。故事写的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一位莫斯科医学教授通过手术把一条狗变成了“人”,而这个“人”却继承了流氓无产者的坏习气:粗鲁、酗酒、偷窃、好色、撒谎、诬陷、告密……并且对教授本人也充满仇恨,最后教授不得不把这个“人”又变成殉。整篇作品文采飞扬,构思奇待,立意新深。
《夜半敲门声》的作者为苏联作家约•格拉西莫夫。小说描写了1949年苏联当局在德国法西斯侵占摩尔达维亚时期的敌伪人员时,迫害无辜,将其强制流放边远地区的悲惨事件。文风直率,朴实无华。
以上三部作品对苏联社会与政治的影响远远地超过了它们自身的文学价值。这几位作家的人道主义信念,道德的激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批评意识和反思意识将给读者一些有益的启迪。
......(更多)
作者简介
漫谈《红木》的作者皮利尼亚克
悠 哉/文
近日,悠哉重读皮利尼亚克的小说集《红木》(石枕川、刘引梅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有些感想。姑且写下来吧——否则日后遗忘了,倒是令人遗憾的不小损失。
先说说皮利尼亚克其人。
这个苏联作家,长期以来不为中国读者所知。但是,实际上,他是大大有名的。据有关资料介绍,皮利尼亚克(1894—1938)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曾经名气很大,担任过苏联作家协会主席,他的小说《荒年》(又译《裸年》)曾经由鲁迅先生译介到中国。可想而知:那是现代中国在“左联”的领导下,大力倡导“革命文学”的时期。
但是,奇怪的是,皮利尼亚克的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属于另类。当苏联诸多作家大肆讴吟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他却偏偏笔走偏锋,哼出一些不和谐的曲调,写一些游离革命文学主潮的题目:偏僻内地小城的沉闷生活,革命势力不曾抵达的地方旧思想和习惯势力,流行于革命高层中的权力斗争和官僚主义,等等。于是皮利尼亚克变成了“用心险恶”和“不合时宜”,不仅多次遭受批判,而且最后落得可悲的下场:以莫须有的间谍罪被逮捕,1938年4月21日遭枪决,年仅44岁。这时候,曾保护过他的高尔基和曾介绍过他作品的鲁迅,都死去了;他的名字和作品,渐渐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苏联文学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不仅恢复名誉,而且其作品被视为“俄罗斯文学的遗产”,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中国新一代读者(例如悠哉)有幸读到他的杰作,更是晚近的事情。
由于中途折戟,皮利尼亚克未能尽展他的文学才华。他的代表作有:中篇小说《不灭的月亮的故事》(1926,又译《不落的明月》)、中篇小说《红木》(1929)、长篇小说《果实的成熟》(1936)等。
我手头他的作品集被冠以《红木》书名,可见这一篇份量奇重。但是,他的另一篇《不灭的月亮的故事》我觉得更好,更能代表他的文学成就。我从乐园论坛上搜索到一篇司马刚的书评,题为《都是〈月亮〉惹的祸》。文章写得很好!苏童在《去小城寻找红木家具》文中却说:“喜欢《红木》的人应该痛恨红木。都是红木惹的祸。”我怀疑,苏童在此耍了小聪明,理由是:
第一,他这个说法,显然套用的是司马刚文章的题目。
第二,皮利尼亚克的惨死,更直接和更重要的死因,显然是他的《不灭的月亮的故事》(讽喻斯-大-林谋害伏龙芝元帅的故事),而不是什么《红木》。所谓“都是红木惹的祸”的“都是”二字,下得颇有些离谱,让人感觉莫名其妙且滑佻轻率,显示了苏童没有真正领略皮利尼亚克作品的三昧。
第三,苏童重视《红木》这篇,与他着力经营“枫杨树”天地的借鉴意图有关系。类似的例子还有:苏童推重美国作家克莱恩的《新娘来到黄天镇》、麦克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等。这些可作印证。
作家苏童,原是巧于向西方作家“偷招”的学徒式作家,原创性东西却是寡少。这不仅是苏童的弱点,而且是王蒙、张承志、王小波、余华、陈忠实、路遥、残雪、王安忆……这干人的致命弱点。
中国当代作家普遍患有“贫血症”和“腿肌萎缩症”:前者导致作品思想内容的贫乏;后者导致作品技法的匮乏,须借助外国作家的拐杖才能蹒跚前行。这两大“乏”症不愈,中国文学的前景难免一片黯淡。
那么,是不是说皮利尼亚克的《红木》写得不好呢?
不是这个意思。我对《红木》也是蛮激赏的;但是并不将它置于《不灭的月亮的故事》之上。
据司马刚在上文中介绍,“《红木》是皮利尼亚克的代表作,写于20年代末,作者本来要将它作为长篇小说《伏尔加流入里海》的几个章节,没想却在柏林一家出版社以单行本出版。”
由此想到他的长篇小说《果实的成熟》,我豁然明白:为什么《红木》让我读后觉得有些散漫了——原来它采取长篇小说的叙述笔调!这与欧洲中篇小说的叙述范式(参见海泽的“猎鹰”理论),是大相悖离的。
难道说,中篇小说必须按海泽的“猎鹰”理论某局布篇,才算好的?中篇小说以散漫形式来写,难道就不行?
也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只是说:它让我弄清楚了《红木》之所以写成这样的原故。
《红木》的情节线索,大致如下:
别兹杰托夫兄弟是莫斯科一对从事古董生意的兄弟,他们乘坐火车到某偏远县城来收购红木家具。他俩落脚在80多岁的老汉斯库特林家。斯库特林见多识广,待人处事随和,家里常常有来访的庄稼汉。有个叫瓦西里的“疯子”常来找斯库德林,他自称是祖国的敌人。斯库德林有个同胞兄弟伊万,他是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曾经混进革命队伍,如今梦想有一天重回党的怀抱,以此混混吃喝。斯库德林还有两个跟他年龄相差悬殊的胞妹,是专门制作衬衣的女裁缝。姐姐卡皮托莉娜是个守身如玉的老处女,妹妹里玛却是放荡形骸、不知检点。就在别兹杰托夫兄弟抵达该县的时候,斯库德林的大儿子、工程师阿基姆也回来了,他是负气离家出走的……
通过以上简介,我们不难看出:小说没有核心故事,只是通过别兹杰托夫兄弟到某县城购买红木家具,串起许多人物及零散的事件,为读者展现了一幅苏联早期内地城镇的生活画面。
而这个“准长篇小说”的构思,实际上袭用的是果戈理《死魂灵》(商人乞乞科夫乘坐马车下乡购买死去农奴的名单;不同的是,他们兄弟俩乘坐火车下乡)的创作构思,原创性并不太强。明了这点,大家也就明白:为什么悠哉对《红木》这篇略显不满了。
至于《不灭的月亮的故事》这篇,那真是写得太好!思想锐利——具有震撼性!——技法圆熟,代表了皮利尼亚克小说的最高成就。限于篇幅,在此我不详述。敦促大家自己研读去吧!
皮利尼亚克的小说善于择取象征意象。例如小说题目中的“红木”和“不灭的月亮”,均带有象征性。读后掩卷咂寻,真让人遐思翩跹,有“忽焉在前,忽焉在后”的余叹。
2008-8-21
......(更多)
目录
读书文摘
......(更多)